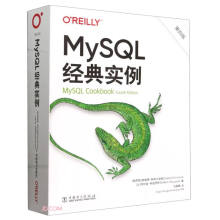《喊叫与耳语》阿格尼丝内心独白的段落,把整部电影的调子定了下来。一个与父亲相仿的女儿,因为相仿而招致母亲不满。家庭看不清的禁忌、猜疑、嫉妒、孤立与仇恨造就的暗礁比比皆是。看似不经意的伤害,变成了一生抹之不去的阴影。在家庭里,不存在饶恕、谅解与宽容。女儿需要爱的理解、信任并渴求爱的肯定时,否决的意志迈开了步伐。阿格尼丝最早回忆的是母亲,那是她与世界之间的纽带。这根纽带原本引她到世界中去,但纽带自身捆住了阿格尼丝。
我几乎每天都想到母亲。她爱玛利亚,因为她们在各个方面都如此相像。我太像父亲,这使她不能忍受。当母亲以她轻快、敏感的方式对我说话时,我不明白她的意思。我做了极大的努力,但永远无法使她满意。然后她会感到不耐烦。她几乎总是不耐烦,主要是对卡琳。我从小体弱多病,不引入注意,但经常挨骂的是卡琳,因为母亲认为她太笨,缺乏才智。另一方面,母亲和玛利亚却有那么多可谈的。我老想知道,她们悄悄地说些什么,笑些什么,为什么她们俩在一起相处得那么好。她们总有她们的小秘密,经常捉弄我和卡琳。
我爱母亲。因为她是那么温柔、美丽与活泼。因为她是那么——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她是那么“实际”。但她也能冷淡无情。我常常向她要求爱抚,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她会拒绝我,玩笑开得十分残酷,说她没有时间。然而我禁不住替她感到难过,现在我年纪大了一些,比较理解她了。我真想再见到她,并且告诉她我理解她的厌倦、她的不耐烦、她的惊恐和不肯放弃争斗。
我记得有一次——是在秋天——我跑进客厅;我大概是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一个人在十岁时总有这种事情)。这时我看见母亲坐在那儿的一张大椅子里。她身着白衣坐在那儿,静止不动,两手搁在桌上,望着窗外。她略向前倾,姿势奇特、僵硬。我走到她跟前。她看了我一眼,目光充满哀伤,我差点哭了起来。不过我没哭,而是开始抚摩她的脸。她闭起眼睛任我这么做。这一次我们相互间很接近。
突然,她恢复过来说:“看看你的手有多脏。你在做什么呀?”然后,为感情所驱使,她两臂抱住我,向我微笑并且吻我。我给这难得的爱抚弄糊涂了。同样突然地,她哭泣起来,一次又一次请求我原谅。我一点也不懂;我所能做的只是紧紧地抱住她,直到她挣脱开。她的脸色又变了,笑了一笑,轻轻擦她的眼睛。“多么可笑。”是她说的唯一的话,然后站起来,留下被弄得神魂颠倒的我。
不可理解、遗弃、斥责发生在早年,使一个人不能获得关于爱的信心与责任的理解。
另一则日记与第三节独白分割出电影几个块面。也可以说,伯格曼设想《喊叫与耳语》时,用了独白的断开方法。阿格尼丝叙述的口气与对自己处境的描述,控制着整部电影的节奏与呼吸。
有时候我想用我的双手蒙住我的脸,永远不再拿开。我是怎样地与孤独搏斗啊?漫长的白昼,寂静的黄昏,失眠的长夜。我拿所有这些倾泻给我的时间做什么?于是我感到绝望,并让它折磨我。我发现,如果我试图避免它,或把它关在外面,一切就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最好还是敞开你自己,去接受折磨,让它伤害你。最好还是不要闭上眼睛,或躲避它,像我以前所做的那样。
虽然,当我写到孤独时,我是不公平的。安娜是我的朋友和伴侣,我想,她比我更孤独。毕竟,我可以用绘画、音乐和书籍来安慰自己。安娜一无所有。有时,我试图跟她谈谈她自己,但这使她羞怯、沉默。
十一
阿格尼丝在《喊叫与耳语》中就是《秋天奏鸣曲》中的海伦。关于海伦的病因,《秋天奏鸣曲》中伊瓦最有资格做出解释。但这种解释于事无补,只能让伊瓦走上从事写作这种内心倾诉的道路。《喊叫与耳语》中的阿格尼丝在独白中说了内心倾诉的奥秘:“我仍然在画画、雕刻、写作、弹奏。早先,我总想象我的创造会使我和外部世界接触,从而不再孤独。而今我知道并非如此。到头来,我的全部所谓艺术表现,只不过是对于死亡的绝望的抵抗。虽然如此,我仍坚持下去。除了安娜,没人看到我的成果。我不知它是好是坏。也许是坏。毕竟,我只看到这么一点点生活。我从来没想过到人们的真实中去生活。虽然我怀疑他们的真实是不是比我的更实在——我指的是我的病痛。”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