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当一个行为者试图发现某情境的适度之处时,他必须承认该情境是在一个群体生活中产生和存在的,所以该行为者所要发现的(甚至他所能发现的)“适度之处”,只能是被该生活群体所规定、所确认的“适度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适度”本就蕴涵着“适于生活群体的伦理要求之度”、“与生活群体的伦理诉求合拍”的含义。
假如行为者所揭示的实践状况,与整个群体的判定发生严重的冲突,那有可能意味着两种情况:(1)他的发现和揭示是不恰当的、不能为群体所理解或接受(比如,某人认为,在现代社会,在一个遇见杀父仇人的情境中,最恰当的行为反应是自己动手取他性命);或者(2)他的发现和揭示虽然恰当,但这个社会本身出了问题(风气败坏、制度腐烂或民众遭到愚弄),不喜欢他的发现和揭示,进而酿成戕害良知与真理的历史悲剧。
就情况(1)而言,这恰好表明,共同生活中的伦理共识有效地发挥了检测功能:对行为者是否揭示当下情境的真实状况、是否选择了适度的行为反应进行检测。由此可见,行为者在具体情境中所确认的“当下确定性”的成立与否,是多么地依赖于更广泛的伦理共识。而对情况(2)来说,这种情况并没有证明,行为者对当下情境之真实状况的揭示就跟群体的认可无关。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该行为者没有获得群体的认可,所以他才会力不从心而寡不敌众。对该行为者而言,由于他认为自己揭示了道德情境的真实状况,因此,他的最大期待恰好就是得到群体的共同认可,而且他也必然坚信,自己的揭示与判断将在一段更长的时间中获得(比自己所处的社会群体)更多的支持(所谓“历史会证明我是正确的”)。即便是对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也只有当我们认为天下确实会有大多数人赞同他的看法,或者说,只有当我们认为他的看法能与一个更广泛、更健全的伦理共识相合拍时,我们才会觉得“他确实揭示了真实状况,而犯错误的是他所身处的社会”。所以说,情况(2)同样(只不过是从反面)表明,行为者在当下情境所确认的“当下确定性”对于普遍伦理共识具有强烈的依赖性。我们无法抛弃这种依赖性。在情况(2)的局面下,我们只能责怪当时的伦理共识是扭曲的或荒诞的,而我们需要做的,则是改善这种共识以获得一种新的共识。只有在更完善的伦理共识出现之际,该行为者才能充分地证明自己真的揭示了当下情境中唯一确定的真实状况;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能回过头去证明先前的伦理共识是虚假或错误的。但无论如何,关于当下情境的真实状况(当下确定性)的实践判断要想成立,就总得基于这样或那样的伦理共识之上。
对于一个有实践智慧的人来说,他的实践推理正是从认识和领悟这些伦理共识而开始的。他的实践推理之所以成功,关键也在于,他能够把自己对于伦理共识的认识和领悟恰当地运用于具体情境--他只有首先承认、尊重并且了解群体生活的伦理共识,才能洞察当前情境究竟在哪个方面、哪个环节上与之发生关联,才能知道当前情境究竟需要他在哪个方面、哪个环节上作出选择,才能决定他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方可与这些共识相匹配与合拍。而这些伦理共识,如前所述,实质上就是基于共同交往而形成的群体生活习俗和伦理规范。在完整的意义上,它的内容包含并表现为关于“幸福”的设想和诉求。因此,承认“幸福”概念在实践推理中的指导地位(大前提),承认“幸福”是来自共同生活中已然形成的伦理共识,井且承认这些伦理共识对于道德哲学的优先性,这可以降低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在具体情境中发生完全相悖的冲突和各说各话的矛盾的危险指数。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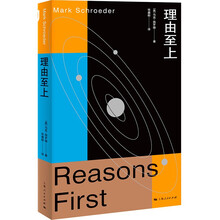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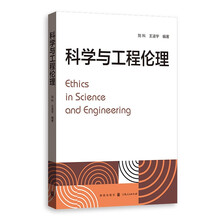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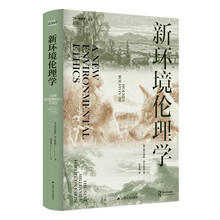
——万俊人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美德伦理学在伦理学的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规范伦理学尽管仍然占有更大比例,但已经没有太多发展空间了,而美德伦理学在伦理学的问题和理论上却有很大的余地。作者对相关的文献有比较充分的了解,能把握该主题的当代发展动向,全书论述清晰,角度丰富,相当出色。
——赵汀阳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