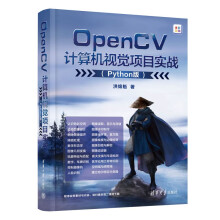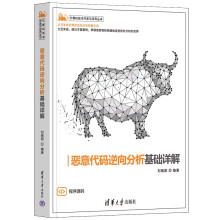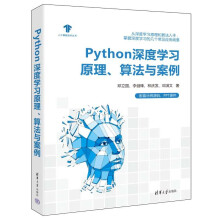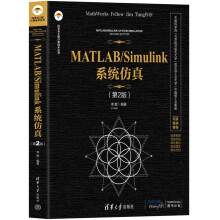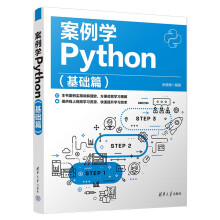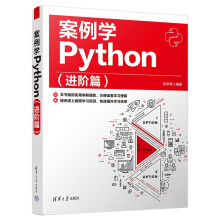第一章(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 “9月1日星期五早晨,那个卖肉的小伙子过来告诉我们:广播里的一 则声 明说我们已经占领了但泽和走廊地带,同波兰的战争正在展开,英国和法 国仍然 保持中立。”维克多·克伦佩勒在9月3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跟伊娃 说,对 于我们来讲,注射吗啡或者类似的东西是最好的归宿,我们的生活已经结 束。” 克伦佩勒是犹太人出身,年轻时皈依了基督新教,后来又娶了一位信 仰新教 的“雅利安人”。1935年,在德累斯顿工学院教授拉丁语言文学的他被校 方开 除,但仍然生活在该市,并且用心地记录着他的亲身遭遇以及周边发生的 事情。 在那两天,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德国人攻击行动的回应依然晦暗不明。“安 玛丽带 来了两瓶发泡酒庆祝伊娃的生日,”克伦佩勒在9月4日记录道,“我们喝 了一 瓶,并决定留下另一瓶到英国人宣战的那天再喝。因此今天轮到喝第二瓶 了。” 在华沙,一所希伯来语学校的校长哈伊姆·卡普兰坚信此时的英国人 和法国 人决不会像在1938年背叛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背叛他们的盟友。在战争的头 一 天,卡普兰就已经感觉到了这次新冲突所具有的世界末日般的本质:“我 们正在 目睹一个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开端。这场战争将给人类文明带来真正的破坏 。然 而,正是这个文明孕育了毁灭和破坏。”卡普兰确信,纳粹主义终将被击 败,但是 战争将使所有人都蒙受巨大的损失。 这位希伯来语学校的校长还意识到战争的爆发对犹太人所造成的特殊 威 胁。同样是在9月1日,他补充道:“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面临着数倍于 此的危 险。只要是希特勒踏足的地方,那里的犹太人就肯定没有了希望。”卡普 兰引用 了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发表的臭名昭著的演说,纳粹领袖在那篇演说中 威胁道,如果发生世界大战,犹太人将会被消灭。因此,犹太人比大多数 人都更加 热衷于参与公共防务的建设:“每当有号召每一位城市居民建隐蔽所以防 御空 袭的命令发布,都会有为数众多的犹太人响应。我也是其中之一。” 9月8日,纳粹国防军占领了波兰第二大城市罗兹:“突然传来了可怕 的消 息:罗兹失陷了!”年仅15岁的犹太青年大卫·希拉科维亚克这样记录道 ,“所有 的交谈都停止了;街道行人渐稀;人们的脸上和心中都为阴霾、冷酷和敌 意所笼 罩。从市中心回来的戈拉宾斯基先生告诉我们当地德国人是如何欢迎他们 的同 胞的。德军总参谋部将要进驻的大饭店里装饰满了各种花环;(德国裔的) 市 民——小伙子和姑娘们欢呼着‘希特勒万岁!’跳上了行进中的战车。街 道上响 彻着大声的德语交谈声。以前被隐藏的与(德意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 关的 一切现在都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还是在华沙,波兰外贸票据交换所的一名雇员同时也是当地犹太社团 的一 名活跃成员亚当·策尔尼亚科夫正在组织成立一个与波兰政府合作的犹太 市民 委员会。“首都华沙犹太市民委员会,”他在9月13日写道,“受到了法律 认可 并在社区大楼中宣告成立。”他在9月23日进一步写道:“斯塔钦斯基市长 任命 我担任华沙犹太市民委员会的主席。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里,这是一个历 史l生的 角色。我将勉力为之。”四天之后,波兰投降了。 在本书中我们将听到许多犹太编年史记录者的声音。这些声音千差万 别,使 我们得以一窥处于毁灭边缘的欧洲犹太人世界的异常多样性。在经历了一 段宗 教传统不可逆转的衰落和文化一族裔犹太性的不确定性不断增长期之后, 已经 找不到对遍布整个欧洲大陆的形形色色自认为(或被认为)是犹太人派别、 社 团、群体以及九百多万个体都适用的明显的共同特征了。这种多样性是在 各自不 同的国家历史、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和以城市为中心的生活的影响之下造成 的。在 面对周围的敌视和偏见时,或者在面对自由的环境所提供的机会时,无数 个体所 采取的不同策略促进了持续的经济变动和社会变动。这些持续的变化造成 了大 流散的犹太人社团内部前所未有的巨大分裂,尤其是在从19世纪末到第二 次世 界大战前夜的几十年间。 举例说来,如何定位罗兹的那位年轻的日记作者希拉科维亚克呢?通 过阅读 他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开始撰写的日记,我们发现了一个深受犹太传统浸润 的工 匠家庭。大卫本人非常熟悉这一传统,与此同时他又对共产主义怀有强烈 的信 仰。(他在稍候写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学校的功课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学 习。”)有着希拉科维亚克这种分裂世界观的不乏其人,相互矛盾的主张在 战争 前夜犹太社会的各种小团体中彼此共存:形形色色大同小异的自由主义者 、社会 民主党人、亲纳粹派、托派、斯大林主义者、各派别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守教的犹 太人围绕无边无际的宗教教条或者“宗族”争执争吵不已。直到1938年年 底,特 别是在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犹太人中竟然还有数千名法西斯党徒。 不过, 对于西欧的许多犹太人来说,主要的关切是在保持“犹太身份”的一些要 素的同 时,与周围的社会实现社会生活同化和文化的趋同,不管那究竟意味着什 么。 所有这些趋势和运动都因国家或地区间的特征以及自相残杀的内部生 存斗 争加倍增长。当然,有时候还要把臭名昭著的个体怪癖也计算在内。老迈 且病人 膏肓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德奥合并(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之后从维也 纳避 难到了伦敦。就在“二战”爆发前不久,他终于亲眼看到了他的最后一部 著作 《摩西和一神教》的出版。就在所有人都感受到不同寻常危险的前夜,这 位经常 强调自身犹太性的精神分析学的奠基人却正在否认他的民族所珍视的一条 信 仰:在他看来摩西不是一个犹太人。 尽管面临着更为巨大的威胁,许多国家的犹太人还是做出了强烈的反 应: “我在本地报刊中读到了你关于摩西不是犹太人的说法,”一位来自波士 顿的 匿名作家咆哮道,“很遗憾你将不能不自取其辱地进入你的坟墓。你这个 老蠢 货……德国强盗没把你送进集中营真是太令人遗憾了,那里才是你归宿。 ” 尽管如此,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犹太人还是有一些根本性的特征 。主要 的分界线是在东欧犹太人和西欧犹太人之间;尽管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地理 的区 分,但其明显的表现却是文化上的。东欧犹太人(除了1918年之后在新政权 提 供的规则和机会下继续发展的苏俄犹太人之外)主要指巴尔干地区的国家、 波 兰、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匈牙利(除了大城市之外)以及1918年之后罗马尼 亚东 部省份的犹太社群。生活在保加利亚、希腊和南斯夫部分地区的主要为“ 西班 牙”(塞法迪)裔犹太人,代表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不同世界。 P2-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