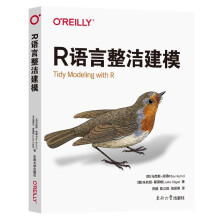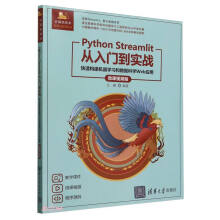一
我们打小就被告知,人类的历史进程是符合进化原则的,先进打败落后,文明打败野蛮,善打败恶,好打败坏,新打败旧……诸如此类。这种灌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使我对后来的取代者都满怀敬畏,因为它们代表的不仅仅是正义和进步,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向。
后来阅世渐深,读书渐多,才发现这样自低向高的进化之路至少在某一时期是说不通的。如魏晋之后的五胡乱华,宋之后的蒙元南下,明之后的满清入关,这些后来的取代者无不是彻头彻尾的落后部族政权,无不是野蛮对文明的颠覆,落后对先进的打击,与所谓的历史进步挨不上边。此外,我们的历史也并非如教科书中所描绘的,一向处在革故鼎新一路前行的进程中,而是除了异族入侵,绝大多数时间在原地打转:
曹丕篡汉建魏,司马氏又篡魏建晋,刘裕又篡晋建宋,萧道成又篡宋建齐,萧衍又篡齐建梁,陈霸先又篡梁建陈。这一路篡下来,前后政权易手了六次,史称六朝。
接下来一出连轴转的好戏,始于宇文觉篡西魏建北周,杨坚篡北周建隋,李渊篡隋建唐,朱温篡唐建后梁。这一次江山易手五次。最后一出篡立大戏始于郭威篡后汉建立后周,赵匡胤又篡后周建北宋。
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闹剧,可以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一句话来形容:“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将要把你抬出去的人,已经站在了门口。”北宋范仲淹有一首诗:“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对于历史的宿命轮回,中外见解空前一致。刘宋末帝刘凖被逼迫退位时,萧道成的帮凶王敬则对他说了一句话:“官先取司马家亦复如此。”(语见《南史?王敬则传》。)一报还一报,报应不爽。六朝人尚佛,是有现实基础的。
新政权取代旧政权后,往往在史书中留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头的缘由其实很简单。
中国历史上的新王朝大都建立在前朝的废墟上,多年的兵连祸结往往造成十室九空、人口锐减。西汉灭亡前的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总人口有5959万,(参见《汉书?地理志》。)经过东汉末的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到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魏蜀两国人口合计不过537万,加上吴国的230万,全国人口总计才767万。(参见《后汉书地理志》注引《帝王世纪》及《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二百六十一年间,生民八余其一。唐代全盛时的天宝十三年(754年),全国人口有5288万,(参见《旧唐书?玄宗本纪》。)到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十年间全国人口锐减三分之二,仅余1692万。(参见《旧唐书?代宗本纪》。)死者不幸生者幸,空出的社会资源需要重新分配,十室九空变成了十室归一,民众得到喘息的同时,又凭空掉下数倍于前的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力想不恢复都难,中间并没有当权者的任何功劳。
小民们在这样的宿命轮回中被王化了三千年,同时也被幸福了三千年。
二
清末启蒙思想家谭嗣同有一句话:“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语见《仁学》第二十七章。明末启蒙思想家唐甄也有类似的一句话:“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语见唐甄《潜书?室语》。)一个说帝王是盗,一个说帝王是贼,合二人之言,所谓帝王者,盗贼而已。
这些发自末世的呐喊,对一个积重难返的民族来说,往往不会有什么振聋发聩的功效。明末有人觉醒了,可是接着整个民族又浑浑噩噩了三百年;清末又有人觉醒了,可是接着整个民族又原地迷离了。历史的罗圈腿教人扼腕,长太息以掩涕。
这些发自末世的怒吼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是因为旧的威权已经垮台,新生政权需要一些开明的言论以区别于旧政权,为自己的“以新代旧”张目。
皇帝对自己的隐身份,却是十分在意的。被赵翼指斥为“盗贼”的明太祖,对与贼音近的“则”字和“强盗”音近的“疆道”都敏感到不行。《廿二史劄记》卷三十二记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之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就把徐一夔斩了。明人宋端仪《立斋闲录》谓:“翰林编修张姓者能直言,不能容,出为山西蒲州学正。例应进贺。撰表,高庙阅之,识其名。见其表词有曰‘天下有道’,又曰‘万寿无疆’,发怒曰:‘此老还谤我,以“疆道”二字拟之。’”
自汉高祖刘邦以诈力权谋取天下始,狡诈和无耻的帝王术就成了王霸之徒的必修课,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才是成就无人比匹的孤寡境地的不二伎俩。我们的历史并不是淘尽狂沙见真金,而是劣币驱除良币,是坏人战胜好人、大坏蛋战胜小坏蛋。坏蛋横行才是中国历史的本质。
三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要“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了下来,最好的都死去了”。
这话也对也不对,最坏的“活下去”是对的,最好的“都死去”是错的。因为权力本不是好人的游戏,好人没资格登上权力的竞技场,偶尔撞上了,也只是历史的误会、上帝的错失,错把一只羊扔进了狼群。刘宋末帝刘凖临难前哀叹“唯愿后身生生世世不复天王作因缘”,(语见《南史?王敬则传》。)话里的无奈与无助叫人唏嘘。南齐废帝郁林王萧昭业也认为:“今见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帅,动见拘执,不如市边屠酤富儿百倍。”(语见《南史?齐本纪下》。)
皮利磨?拉维话里的“好人”,指的只能是相对不那么坏或还没有彻底坏透的家伙,而不是道德层面上的好人。中国古代被谥为和帝、顺帝、恭帝、敬帝、静帝的失败者,单从谥号上就能看出他们大多是现实意义中的弱者,是传统道德层面上的和顺恭敬之辈、清静无为的不争者。晋恭帝司马德文甚至被政治对手赞为“明德光懋”、“众望攸集”(语见《晋书?恭帝纪》。)的大有为之主;刘宋末代皇帝顺帝刘凖,“姿貌端华,眉目如画,见者以为神人”。(语见《南史?宋本纪下》。)
对于小百姓来说,以上诸位或许是羊群中的豺狼,但在王霸之徒眼中,他们只是羔羊,或者至多算是一匹未成年的小狼。
刘宋顺帝刘凖被杀时,虚岁十三。(事见《南史?宋本纪下》。)齐和帝萧宝融被杀时,虚岁十五。(事见《南史?齐本纪下》。)梁敬帝萧方智被杀时,虚岁十六。(事见《梁书?敬帝本纪》。)西魏恭帝拓跋廓被杀时,虚岁二十一。(事见《北史?魏本纪五》。)北周静帝宇文衍被杀时,仅虚岁九岁。(事见《周书?静帝纪》。)如果把他们也归入坏蛋行列的话,那么他们至多算坏蛋中的弱者。刘宋顺帝刘凖禅位时,吓得“逃于佛盖下”。(事见《南史?宋本纪下》。)这位笃信佛陀的倒霉皇帝,在浩劫临门时,能想到的庇护,也唯有菩萨的慈悲了。
四
如果我们了解威权政治的本质,就会对坏人的一路得意有所释怀。
盗亦有道。做一名成功的强盗,也要讲求强盗逻辑,有所为有所不为。当一个按套路出牌的强盗碰上一个完全不顾套路的强盗,失败就变得理所当然。所以当失败的强盗引颈就戮、身死国灭时,往往都会有悔不当初的痛心疾首,后悔当时的一念之慈,痛惜当年的一息之仁。正如韩信被执时,感慨“吾悔不用蒯通之计”,(语见《史记?淮阴侯列传》。)亦如魏徵所说“太子蚤从徵言,不死今日之祸”。(语见《新唐书?魏徵传》。)
不半渡而击、不擒二毛的宋襄公成了千古笑柄,还没坏透的楚霸王乌江自刎,不谙权谋诈术的臧洪身首异处,相对迟钝的李密横死刀下,比较仁厚的李建成一箭穿心,稍为爱民的张士诚挫骨扬灰。笑到最后的是楚成王、刘邦、曹操、刘备、李渊、李世民、朱元璋这类崇尚诈力权术的阴谋家。相对仁慈的一方最终都为自己的妇人之仁付出了血的代价,被自己的不忍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在一个以权谋诈术为主体的社会里,历史只能是坏人的舞台。坏人战胜好人或稍好的人,才是王朝更迭的本质。
我们的教育,一直宣扬成为好人是成就功业的基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试想,如果普天下之人都奉行这一成功学,称王称帝者会多到何种程度?
所以,要想成就王霸之业,首先要成为社会的另类和异数。在好人遍天下时,要努力成为暗中的坏人;在坏人遍天下时,要努力成为明面上的好人。凡事必须跟对手们逆着来,你的成功才能让对手始料不及,这可以算是竞技社会最普遍也最适用的制胜法则。
五
我们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以为只有政治开明才能成就经济上的繁荣,其实并不尽然。乾隆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2%,(参见戴逸的《中国经济的千年态势与复兴之路》。)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也认为中国的GDP在公元1820年占世界的32?9%。比今天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还要大。然而,史称盛世的康雍乾三朝,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政治上却极端反动保守。单乾隆一朝,兴起的文字狱就有一百三十多起。章太炎认为,乾隆朝禁书“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语见《哀焚书》第五十八。)鲁迅也认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语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用万马齐喑来形容当时严峻的政治现实,并不为过。
经济上的繁荣绝不能建立在错误的方法上,以错误方法取得的成就,绝不是百姓之福,只能是百姓之祸。一再重复的历史证明,错误基础上的繁荣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治乱相仍,接续所谓的盛世而起的必然是漫长的乱世。
汉有“文景之治”,但此后见于《汉书》、《后汉书》的“人相食”比比皆是。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春、元鼎四年(前113年)夏,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九月、二年(前47年)六月,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王莽天凤元年(14年)、地皇三年(22年)二月、新朝末年,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安帝永初三年(116年)三月、十二月,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四月、永寿元年(155年)二月,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春正月,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四月至七月、建安二年(197年),皆有此类记载。(参见《汉书?武帝纪、元帝纪、食货志、王莽传》与《后汉书?刘盆子传、安帝纪、桓帝纪、灵帝纪、献帝纪》。)
唐有“贞观之治”,然而见于旧、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人相食”同样层出不穷。就在后人称羡不已的“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那段辉煌时期内,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夏五月,关中地区“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三。)一场自然灾害,便能击垮所谓的盛世。盛唐尚不过尔尔,更别提安史之乱后的末世了。
明有“成宣之治”,然而见于《明史?五行志》的“人相食”惨剧便有十四次之多,天顺元年(1457年),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弘治十七年(1504年),嘉靖三年(1524年)、三十一年(1552年)、三十六年(1557年),万历十六年(1588年)、二十九年(1601年)、四十四年(1616年)都发生过。崇祯朝无疑是明代最为黑暗的时期,崇祯七年(1634年)、九年(1636年)、十年(1637年)、十二年(1639年)、十四年(1641年),“人相食”的惨剧频繁发生。除《五行志》记载的五次之外,《明史》记载崇祯一朝的“人相食”事件还有四次:崇祯六年(1633年),河间“岁旱饥,人相食”;(语见《明史?忠义三》。)崇祯九年(1636年),“山西大饥,人相食”;(语见《明史?庄烈帝纪》。)崇祯十三年(1640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语见《明史?庄烈帝纪》。)崇祯十四年(1641年),左懋第督催江南漕运,道中驰疏:“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语见《明史?左懋第传》。)
崇祯皇帝在位短短十七年,见于《明史》的“人相食”记载便有九次之多,平均一年多便要发生一次。
清代有“康乾盛世”,但见于史料的“人相食”一点也不比前朝少。单《清史稿?灾异志五》所载,便有十四次。
不绝如缕的“人相食”告诉我们,历史传说所谓繁荣,不过是“虚荣”而已。表面的“繁荣”背后,无不掩盖着小百姓们无法承受的惨重代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