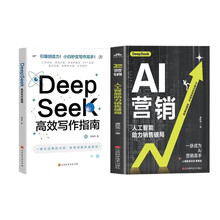我们对于“理论”通常会有数量上的要求。足够多的数量也是能够打动人的。只要你做出了足够多的陈述,别人就会心存“敬意”地对你的陈述做出“理论”上的肯定。“理论”确实在这一种含义上被普遍地使用着,以至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只要做出了足够多的陈述,这些陈述就似乎一定是“体系化”的。
但是,足够多的陈述是否自然地就能实现“体系化”,这是值得怀疑的。所谓“体系化”,按照日常的要求,至少应该是:这些陈述是彼此关联并且相对自洽的。当然,对“体系化”的严格的要求是“逻辑化”,即,你的所有被称为“理论”的陈述,彼此之间应该形成逻辑的推论关系,就是说,从某一陈述或者某一意见出发,将能“必然地”推导出其他的陈述与意见。这种情况只存在于数学与少数的自然科学当中,大多数自然科学,比如生物学,都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因此,对于像教学一类有关人类事务的陈述,只能指望它们达到较低层次上的“体系化”要求,即彼此关联并且相对自洽。
不幸的是,即使是这种较低的要求常常也只是某种奢望或错觉。我们能够见到的很多陈述,尽管它们被令人感动地堆垒在了一起,但说它们是彼此关联的和自洽的,却十分困难(这种状态当然也是对笔者当下叙述的准确描述)。所以克尔恺郭尔才俏皮地写道:如果我能见到理论体系,“我会像别人一样愿意屈膝跪拜”,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成功。有一两次我几乎就跪下来了,就在我以免弄脏裤子把手帕放在地上的时候,向理论家提出一个天真的问题。我问:“请坦率告诉我,理论彻底完成了吗?因为如果是,即使弄脏裤子我也要跪拜这个理论。”但是他们总是回答说:“不,恐怕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所以体系再次迟到,我的跪拜不得不再次推后。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