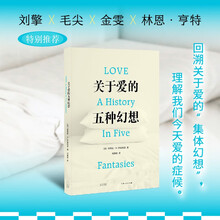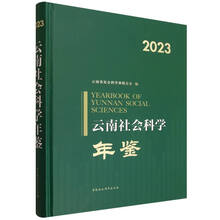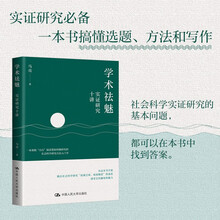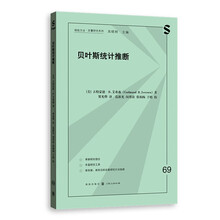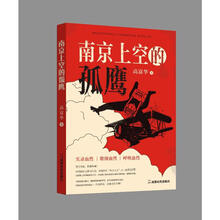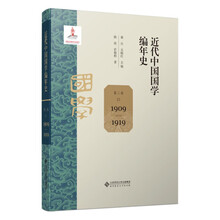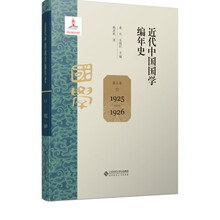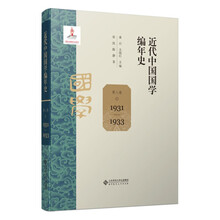如果将观众的收视行为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不难发现影响收视行为的受众因素包括:①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如观众是生活在传统社会中还是现代化都市中;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与媒介相关的需求,如希望收看新闻资讯还是只想娱乐消遣;个人品味和偏好,如是喜欢小资情调,还是崇尚朴实自然,品味与偏好包含着群体文化及阶层内涵;闲暇时间的媒介使用习惯,如喜欢读书、看报还是看电视,在电视收看时习惯于仪式性收看还是工具性收看;媒介使用的具体环境,如随着电视内容接收终端的多样化,电视收看的空间选择自由度增大,继而将影响受众的使用模式与内容选择;时机,观众收看到某一节目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现实性转化在于电视节目的编排与观众时间安排的巧合等因素。
同样,影响观众电视收看的媒介因素也包含了多个层面的内容,如媒介系统的社会功能定位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媒介供给结构。媒介结构决定于宏观的制度安排,从西方国家的传媒经验来看,以公营电视为主的电视系统会提供更具多元化选择的节目,而在商业电视主导的电视供给结构中,媒体更倾向于提供具有高收视潜力的大众性节目。由此延伸的另一个影响因素表现为观众可获得的内容选择,这决定于很多更具体的内容,如是否能收到某个频道,能看到什么样节目——有时即使不喜欢某类节目,但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而使观众不得不“被动选择”不喜欢的节目,哈耶克曾用“穿越田野的人行道”来喻指那些没有人代表他们的特殊观众。
②此外,媒介宣传、节目的时间安排及其呈现方式等也会对观众的电视节目收看在相对微观的层面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
以上勾勒了收视行为是怎样产生的,这些基于社会文化环境与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子说明,观众收看行为有其必然与偶然的原因。通过获知其必然性因素,则有可能准确定位忠实的观众。
媒介效果研究传统形成之初,受众被认为是缺少理性的、被动的乌合之众,在这种理念下,观众是没有忠实与不忠实之分的.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媒体”(这里指当时是新媒体而如今已成为传统形式的电影、广播和电视)在生活中的日常化使用,人们发现受众远不是最初想的那样。当媒体的强效果模式成为过去式,主动的受众观被普遍接受。主动的受众最有可能在自我意识与需求的支配下成为频繁转台的电视观众,同时也最有可能在收视需求被充分满足的前提下成为最忠实的群体。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