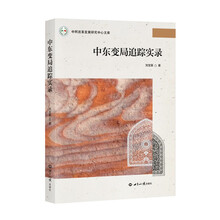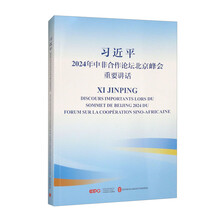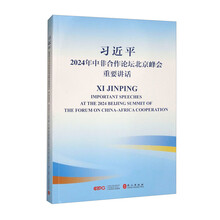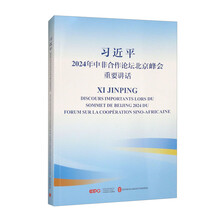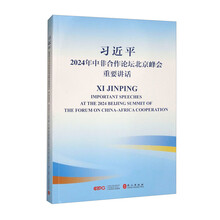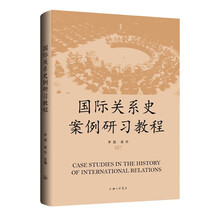美国是一个十分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它历来讲美国的特殊使命和命运,讲美国例外论,强调美国价值观念的普世意义,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建筑在美国的价值观念之上是美国决策者的口头禅。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并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克林顿政府把推广民主作为外交政策的三个支柱之一。到了乔治·沃克·布什时期,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被强调到了极致,推广民主被视为美国外交的终极目标。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赖斯国务卿的许多讲话都不厌其烦地阐述这一点。公共外交为何在乔治·沃克·布什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呢?笔者以为起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冷战的结束被许多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看作是美国意识形态对苏联意识形态的胜利,他们兴高采烈地庆祝美国单极世界的到来。但恰恰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地悄然出现了“反美主义”。这实在是令美国决策者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在他们看来,美国的价值观念比别人的都好,美国是善的代表,美国所做的一切是在“替天行道”,为何会有这么多的人对美国不满,甚至反对美国?在“9·11”以后,布什和一些美国高官一再问:“他们为什么反对我们?”国务院还主持了两次关于全世界反美主义的专题讨论会,一次是穆斯林世界学者的会,一次是非穆斯林世界学者的会。笔者应邀参加了后一个会,它于2002年9月在马里兰州举行。与会的国务院高官总结说,在穆斯林世界的反美主义是仇恨,在非穆斯林世界的反美主义是不满。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