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联姻之所以呈现日益不稳定的特征,其原因也许在于激进个人主义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进步运动的影响,它们使得私人的身份和个人的自主成了“最高的善”。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例如英国,所有类型的权威关系都受到质疑,不管这种关系是基于资历还是公职,法律还是习惯,阶级还是性别。所有制度上的联系,在潜在的意义上,都被视为压制性的。甚至福利政策也受到怀疑,从好处说,它体现了一种家长作风,因此与独立自主毫不相容;从坏处说,也是十分险恶的,它被左翼指责为社会控制的手段,被右翼称为假公济私的虚伪形式。当前,对投票的迷恋,以及“一人一票”口号的流行,被视为促进各党派和工会积极参与的良方,这恰好说明了各种观点都在起作用这样一种混乱不堪的情形。作为货币主义经济中消费者权威的政治对等物,对投票的迷恋得到右翼的支持,却使左翼和工会运动处于混乱之中。然而,由于它主张,进行决策的应该是独立自主的个人,他应该运用个人的判断力,并作出自己的选择。这就和主张把个人放在首要地位的左翼的解放主义政治非常相似,即个人要有他所应得的“做自己的事情”的神圣空间。于是,在政治谱系的任意一端,都流行着权利的语言和对独立自主的多元主义的关切。
激进个人主义不但挑战了权力结构,而且还隐含着对集体根基的质疑。从理念上说,社会是一个没有疆界的开放空间,个人可以在其中自由地、任意地流动。集体,不再像在团结或服务、公平分配或平等那样的观念中被视为实现共同利益的手段,而是被视为强制的工具,它要促进的是统一性而不是多样性,它胁迫个人,使少数派服从于没有思想的大众。所有的统一化制度和整体性观念都遭到了这种抨击,但是,正是跟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有关的那些制度和观念似乎特别不堪一击。一旦罢工的决定变成了个人决断的问题,而不是服从集体纪律,或维护集体荣誉的问题,它就必须经受所有差异性和不同政见的考验,这就使得它逐渐变得难以解决。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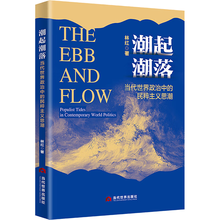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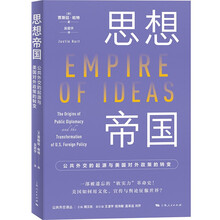


——格雷斯·斯塔德曼·琼斯(《独立报》)
塞缪尔生来就适合做一个历史学家。他具有那种极其重要的品质,能够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从公众健康到殖民地的反抗,从街道照明到街头斗争,所有的一切都能激发起他的兴趣。
——《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