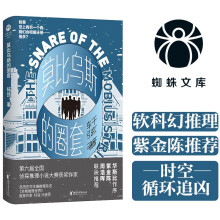三、男人幻想中的“三合一”型女性
(一)很多男人都有“圣母妓女情结”
男人这种绅士流氓相混合的双面性格很可怕,它决定了很多男人都有“圣母妓女情结”。
奥地利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他的经典作品《爱情心理学》一书中,就非常详尽地分析了男人这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圣母妓女情结”:凡是那种纯洁善良的女子,他们不会动心,情爱的诱惑力永远来自那些贞操可疑、性生活不太检点的女子,比如红杏出墙的有夫之妇,堪称大众情人的青楼艳妓。对他们来说,女人越是轻浮淫荡,他们越是爱得发狂。只有这样的女人,才会让一个男人真正体验到“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快活。一旦疯狂爱上之后,他们又幻想这个女人只忠实于自己。想把大众情人据为己有,无疑等于把公共财产中饱私囊,显然这种爱情的获得就像偷运珍宝的过程,既危险又刺激,而其中的艰难困苦,更会激起男人无穷的斗志。
男人面对这种交际花型的大众情人,常常还有种幻想,她可能身处险境,她渴望逃离虎口,他如果不及时伸出援手,她就会落到更加悲惨的境遇,于是他身上潜藏的英雄气概被唤醒,他要手拿钢枪,去为她战斗,他要英雄救美,拯救她于水火之间,“坏女人”会让一个男人瞬间体会到自己内心的强悍。在很多古典小说上,一些平日里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书生和公子,一见到沦落风尘的美貌女子就心生同情,就想帮她赎身,甚至冒着极大地风险和她同生共死,就是出于这样一种奇妙的心理。
这种“圣母妓女情结”在婚姻中就集中体现在当妻子怀孕或是生产以后,他们很难和一个有“母亲身份”的女人持续做爱。他们潜意识认为,一旦他们的妻子成为母亲,就很难再让他们产生性欲,因为母亲是纯洁无暇的,神圣不可侵犯。奥地利心理学家奥托-魏宁格在他所著的《性与性格》一书中指出:“在男人眼里,母亲似乎更接近于贞洁的理想。”。
在人的潜意识中存在一种观念,即肉体之爱更接近于动物,只能和坏女人或坏男人发生;精神之爱接近于人,应该存在于真爱之中。所以为了满足性欲,他们只好把目标转移到其他女人身上。有古希腊雄辩家之称德莫斯特尼斯的话为证:“我们拥有妓女为我们提供快乐,拥有侍妾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而我们的妻子则能够为我们生育合法的子嗣,并且料理家务。”这种男人把妻子视为母亲与“好女人”的象征——圣母,同时他们也视“坏女人”(妓女和情人、小三儿)为性爱的对象——是“妓女”;这也许是“好女人”的悲剧,他把尊重、感激给了你,甚至把你神圣化了,却把鲜活的性和爱给了“坏女人”。
前面提到的“良家妇女综合症”在这里终于找到了病因:男人都是绅士流氓的混合体,所谓良家妇女只满足了男人一半的心理需求——他的绅士情怀:娶个体面的淑女回家,过起光鲜的中产生活,而他另一半的流氓心态却无从宣泄,一旦在刻板的婚姻课堂里呆久了,不少男人就想逃学,就想到外面找个“坏女人”过把流氓瘾。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男人的圣母妓女情结导致了“良家妇女综合症”的爆发。这也是如今“无性婚姻”越来越多的一个重要因素。
易中天先生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男人的性心理是很矛盾的,他希望自己的女人严守贞操,其他的女子最好都是娼妇。”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自己的女人过于矜持过于保守,他又会觉得索然无味,他又蠢蠢欲动想到外面去尝尝野花的香味;倘若外面的女人过于随便过于开放,他又会觉得忐忑不安,因为跟家里那位贤良淑德比,外面的这位又过于花枝招展了,似乎为人妻为人母又不够大家闺秀,男人就是这副德性,得陇望蜀又难忘旧爱,有了新情人又不舍糟糠妻,(这也是很多男人只外遇不离婚的心理因素)。女人都应该矢志不渝从一而终,至于男人,那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二)男人的“圣母妓女情结”影响了中国的传统婚姻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男人的这种“圣母妓女情结”影响了五千年中国传统的婚姻生活史。
绝大多数人在情感需求方面都存在一种补偿心理,缺什么找什么。(关于这点,我会在第三章有进一步论述)古代文人缺的是什么,一曰爱情,二曰风情。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模式讲求的是“明媒正娶”,即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的家长给儿女提亲首先考虑的是不是门当户对,其次怎么样传宗接代,至于爱不爱,情不情的反倒不太重要。
在这种包办婚姻的情形下,男女结婚无异于“圈养牲口”,两个素不相识全无感情的一对男女,甚至在此之前连面都从未见过,晕头转向地拜了天地,稀里糊涂地进了洞房,从此一张床拴住了两个陌生的男女,这样的婚姻只关乎门第无关乎爱,只关乎生育无关乎性,由此,“无爱之婚”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最常见的婚姻状况和婚姻方式了。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无非两个目的:一要生孩子,二要过日子,礼法上不还说吗?“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阃就是大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既然男主外,丈夫就老老实实把外面的工作做好,没必要把它带回家里,妻子就本本分分当好“内当家”,也无须拿到公众场合去说,一句话,家丑不可外扬,发展到后来,丈夫劳累了一天回来,不跟妻子诉苦成了“很男人”的表现,而妻子受了婆婆和姑嫂的夹板气也学会打落门牙往肚里吞。于是,夫妻俩口子除了见面说句“吃了吗?”“睡觉不?”也没啥好说的了,“哑巴夫妻”渐渐成了传统婚姻模式下夫妻关系的悲剧。
既然中国传统的婚姻只看门第,只重生育,所以夫妻之间有无感情以及性生活是否和谐就显得无关紧要了。甚至,在“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思想的熏陶下,妻子的性冷淡就是“不淫”,丈夫的性无能就是“不色”,前者为淑女的标志,后者乃英雄的本色。这种不色的丈夫和不淫的妻子组成的家庭显然是符合“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理想婚姻模式的。虽说才高八斗财大气粗的男人都有条件纳妾养婢,但妾和婢是什么?是家里的二等公民,和主人是典型的主仆关系,连地位都不平等,男人即使获得了一时的性满足,也免不了怅然若失。有时候,男人需要一个在地位上和他平起平坐,在心灵上和他平等对话的红颜知己,这显然是一天到晚在家里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的妻妾所无法满足的。
既然缺什么就去找什么,任谁都有爱的需求,情的渴望,更何况是一个风流倜傥满腹经纶的才子?整天对着家里的“泥塑木雕”难免意兴阑珊,他们需要浪漫,更需要刺激。于是外面的花花世界,就成了我心狂野的文人骚客们流连忘返的绝佳去处。而偏偏生长在青楼里的诸多姊妹花又是那样的顾盼生姿光彩过人:她们不仅美貌如花而且天资聪慧,侠骨柔肠,更重要的是她们大都博览群书,出口成章,才华横溢,一专多能——一个小有名气的青楼名妓,往往身兼歌手、舞蹈家、琵琶和古筝演奏家、诗人、作家、心理医生等多重身份,最起码也是一个文学女青年,随便举个例子:宋代名臣赵忭,在成都为官之时,有一回出游在街边看到一个头戴杏花的妓女,顿生好感,赵忭随口吟出了一句诗:“髻上杏花真有幸”,谁料那美眉星眸一转,应声答道:“枝头梅子岂无媒!”惊讶得咱们这位赵大人差点从马上掉下来,这句诗对的确实妙啊!“杏花”对“梅子”,“有幸”对“无媒”,“杏”与“幸”同音,“媒”和“梅”同韵,真是对仗贴切意味深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妓女尚且如此,何况是许多美名远扬的大牌妓女?
自古磨难出英雄,妓女何尝不是这样?在风月场中摸爬滚打大半辈子,她们比娇惯的千金小姐,比寻常的名门闺秀更懂得世态的炎凉、人心的叵测,也知晓友谊的轻重、爱情的价值,身处冷暖人生,她们反倒像一个“灵魂处女”,永葆纯真的本色。表面上打情骂俏,实际上义重情深,逢场作戏是假,渴望从良是真。林语堂认为:“妓女较之家庭妇女所受教育为高,且她们较为独立生活,更较为熟习于男子社会。”易中天总结:“寻花问柳,偎红倚翠,对于文人才子,变成了一种风流雅事。金榜题名春风得意时,在这里听‘小语偷声贺玉郎’,自然风光得很,时乖命骞失魂落魄时,在此寻访得一二红粉知己,又何尝不是一种补偿?”
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鼓励男人都要去找妓女,也不是赞美文人墨客这种不负责任的腐朽人生,而是分析中国男人奇特的情爱心理,为什么放着家里的贤妻不爱,偏偏要到外面去风流快活?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中国古代的情诗基本上都是文人写给妓女,那有没有表现夫妻之情的诗篇呢,有,但多半是写给亡妻的。比如潘岳的《悼亡诗》,比如苏轼的《江城子》。妻子在世时无诗可赠,死后才写诗悼亡,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吧?估计这是传统文化不许夫妻之间过于亲密所致。要不怎么总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呢?夫妻之间很少情爱,男女之爱在婚内无处宣泄,只好移情别恋。
我发现,中国古代真正的爱情,多半不是在婚前,就是在婚外,很少在婚内的。所以,文人墨客只好流连青楼与各色名妓唱和酬答,养在深闺人不知的淑女贤妻们也不甘寂寞,索性“红杏出墙”寻找真爱,就形成了中国传统婚外恋的两大基本模式。对男人来说,妻子为正,必须正经严肃,不可调笑,情妇和妓女既然非“正”,自然不妨打情骂俏放浪形骸。男人的“圣母妓女”情结在就是这么来的。
(三)男人总幻想有一位融圣母、处女、妓女于一身的完美女性
不过,男人的情爱心理有时候也很矛盾,一方面,他有圣母妓女情结,另一方面,他又幻想他爱的女人既有贤妻良母的温柔大度,又有红粉娇娃的春情荡漾,还得保持纯情玉女的纤尘不染,她也许身体上早已失节,灵魂上却从未失贞,在外面她似乎人尽可夫,关起门来又只对他一人忠诚,她有时候像荡妇一样风骚入骨,,有时候又像母亲一般无比包容。总之,男人内心深处完美女人的形象——或者是一个有着风尘气息的良家妇女;或者是一个外表清纯的欢场女子,前者在西方文学名著中俯拾皆是,如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后者则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中随处可见:杜十娘、董小宛------我认为,这种融处女心态、恋母情结和青楼狂爱于一身的“三合一型”女性才是男人最理想的梦中情人。
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舞台上的那些流芳百世的青楼名妓——无一例外不是这种“三合一型”的女性形象。比如苏小小,很小就开始倚门卖笑的皮肉生涯(身份上属于红粉娇娃),传说她曾在西湖边上偶遇一位穷困书生,便慷慨解囊,赠银百两,助其上京赶考(心理上很有母性情怀)。但是,情人从此未归,苏小小并没有成为怨天尤人的秦香莲,而是从对情的执著大踏步地迈向对美的执著,从不守贞节到只守“美”,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激起男人的拯救欲)。最后,重病即将夺走她的生命,她却恬然适然,觉得死于青春华年,倒可给世界留下一个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认为,死神在她19岁时来访,乃是上天对她的最好成全(如同冰清玉洁的处女一样让男人永世难忘)。难怪年纪轻轻就香消玉殒的苏小小成了中国名妓史上的一座丰碑,她的香冢至今立于西子湖畔,为名胜之一,每年骚人游客,凭吊其旁者,骆绎不绝。
还有蒲松龄老先生笔下那些经典的“狐狸精”们,并不都是红颜祸水祸国殃民,相反,她们风情摇曳,风姿绰约,多情妩媚,急公好义。当那些落魄书生、落难公子每天衣着寒酸食不果腹的时候,不知从哪儿走来了一群狐狸精模样的女鬼,表面上她们都像定时炸弹一样危险(她们有的喝人血,有的吸阳气),可一旦爱情的神话从天而降,她们就摘掉了魔女的面具:长得如花似玉不说,还特会做饭!更绝的是,她们从不居美自傲爱慕虚荣,不会缠着身边的男人买这买那,反倒甘当贤内助,具有雷锋叔叔和张海迪姐姐那样的奉献精神,而且危难之处显身手,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不时上演一出让普天下男人为之感激涕零的“美女救书生”的好戏,而且她们还特别通情达理,知道什么时候该来,什么时候不该来,男人寒窗苦读的时候,男人金榜题名的时候,男人和正牌妻子比翼双飞的时候,她们绝对不来捣乱,即便和有情郎不能终成眷属,也绝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而是含笑离去光荣引退--
如果你认为只是中国男人有狐狸精情结,才会凭空杜撰出这种十全十美的女性形象,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翻翻西方的经典文学名著,这种集圣母、荡妇、处女于一身的“三合一型”女性也层出不穷,而且清一色出自男作家的“白日梦”中。
法国作家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虽说沦落风尘,外表却像处女一样清新可人,因为被爱情所拯救,最后从妓女蜕变为一个圣母,一个牺牲自己拯救阿尔芒灵魂的圣母,象茶花一样美丽的圣母;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作《罪与罚》中有个18岁的妓女索尼娅,为了帮贫苦的父亲还债,在街边从事最低等的卖淫活动,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第一次见到她,心中升起的是一种怜爱之心,觉得她像个处女一样楚楚可怜。拉斯科尔尼科夫无意中杀了人,为了让他投案自首,索尼娅总是不厌其烦地开导他,规劝他,突然有一天,拉斯科尔尼科夫发现这个幼小而孱弱的身体里突然放射出一种强大的光芒,一种近似圣母般温暖的光芒,这个总是桀骜不驯的年轻人一下子感受到了爱的滋养,他心中人性的一面复苏了,他决定自首—
男人心目中,女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汇,女人对男人来说,象征着母爱、情爱、性爱,是肉欲、情欲、性欲纠合在一起的复杂混合体。男人从小在母亲的怀抱中成长,母亲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所以他会刻骨铭心;进入青春期,班上或邻家可爱的小女孩会走进他的视野,她像白莲花一样纯洁无暇,代表了一个男人对外面世界的美好向往;步入社会后,由于竞争激烈,男人的生活像条狗,一个浑身如玫瑰般带刺的“坏女人”又让他被压抑的原始激情得到释放。
男人一生总在这三类女人当中徘徊选择,有时候他又幻想这三类不同味道的女人全部集中在一个女人身上,满足他多方面的心理需求:在纯洁的像白纸一样的玉女面前他是经验丰富的大男人,在圣母一样无私的女人面前他可以放下大男人的架子,做回顽童,在荡妇面前他的流氓基因又尽情展现。因此,男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女人大多是这种“三合一”的混合角色。没办法,男人骨子里有时候就是这样的贪得无厌。
以前有种说法,男人都是处女情结很重的,都想娶个处女,我认为这种说法非常可疑,(前面提到,一个女人婚前经历过于简单,在婚后很容易陷入良家妇女综合症,让男人审美疲劳)其实男人需要的是那种内心纯洁,但是行为放荡,且思想又很高尚的这样一种复杂混合体,所谓“客厅是贵妇,厨房是主妇,卧室是荡妇”就是男人对一个理想妻子的痴心妄想。只可惜,这种女性形象是男人单相思的产物(以上提到的这些经典的三合一形象全是出自男性作家笔下),纯属一种不靠谱的性幻想,完全是白日做梦!也极其荒谬可笑!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不是无处可寻,基本上也属凤毛麟角。所以无奈之余,男人只好“人格分裂”,婚姻里找个圣母型的淑女,婚外再找个荡妇型的欲女,某种程度上,男人的“圣母妓女”情结相对于“三合一型”的理想女性,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情感选择。
其实,女人也有类似的完美情人模式,我曾经听不止一个女人说过,最有魅力的男人是亦正亦邪的。他有坏的影子,但现在又是好的肉身。他外表坏坏的,心地又好好的,他过去是流氓,现在是绅士,偶尔又是顽童,就像古龙笔下的江小鱼、金庸笔下的谢逊、黄药师、韦小宝。
(四)女人的“圣徒罪人”情结导致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很多男人有“圣母妓女情结”,不少女人也有类似的“圣徒罪人情结”:那就是女人把丈夫视为“圣徒”,产生不了爱的火花,却在坏男人(罪人)的引诱下激情澎湃,难以自持。《红与黑》中的德瑞纳夫人被于连勾引,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跟奴仆私通,都是因为丈夫太“正人君子”了,太不懂得体贴妻子了,女人心中爱的火花就逐渐熄灭,此时遇上一个情如火焰般高涨的野小子,女人心房里攒了多年的干柴就会迅速点燃,于是就跟着那束火焰去了。这个世界上,只要是个人,无论男女,骨子里都想冲破道德的藩篱,回到最原始的激情状态,哪怕一次也好,尤其被道德的卫士禁闭已久的淑女少妇更是如此。
还记得电影史上那艘不沉的巨轮“泰坦尼克号”吗?一个丰腴的富家女罗丝,能买得起昂贵的头等舱船票,一个清秀的穷画家杰克,只能靠逃票才能登上泰坦尼克号。但这两个地位悬殊的人,偏偏在船上一见钟情,直至爱得死去活来爱得天翻地覆。
这是为什么?
因为顽皮的杰克会教她怎样放肆地“吐口水”,会带她冲到船头学大雁展翅高飞般地眺望大海,会目不转睛深情款款地告诉她:“你跳我也跳!”而陪伴在罗丝身边的那个衣冠楚楚的未婚夫,除了上流社会的拘谨刻板、除了道貌岸然的虚伪自私,一无所有。杰克的不期而遇,让这个手中握有繁华,心情却始终荒芜的淑女一下子发现了生命的“绿洲”,发现生活还有像野百合般芳香馥郁的另一面。虽然快乐是那么的短暂,但在那艘船上他俩却拥有了整个的世界,这段爱情也在罗丝心中成为了永恒――
对罗丝来说,她不爱未婚夫,却跟杰克心有灵犀,就是“圣徒罪人”情结的表现。
女人这种“圣徒罪人情结”还会导致更为奇特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它来自1973年发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桩银行绑架案。此案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此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四名受害者不仅不恨歹徒居然还深表同情——原因时绑架期间歹徒非但没伤害他们还对他们施以照顾,更离奇的是,一名女人质竟爱上了其中一名绑匪,在绑匪刑满出狱之后,还跟他结了婚。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要害在于:加害者处于完全优势的情况下,被害者不能逃离加害者圈定的博弈系统。加害者行为在本质上的不正当就被忽略,而生存第一的首要目标就会导致被害者产生合作的行动,继而产生依赖乃至依恋的情感。有人还把这种综合症称之为人质爱上绑匪的特殊情感。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司空见惯的淑女爱上强盗,小姐跟流氓私奔、白面书生迷上狐狸精,其实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作祟的结果。
对于一个在温室里长大的小花来说。突然遭遇暴风雨的袭击,她的心情是既恐惧又兴奋,既害怕又好奇,所以很多胆小如鼠的女孩子反倒喜欢看恐怖片,一些手无寸铁孤苦无依的盲女会爱上劫持她们的杀手,就变得顺理成章了,犹如一向紧闭的房门突然打开了一个缺口,房子自然摇摇欲坠,心灵的缺口被强行打开,恐惧中原来的价值系统坍塌了,但新的秩序需要重建,此时高高在上的强者自然主宰了一切,不知不觉中,弱者心甘情愿成了任其摆布者,倘若对方的威严中流露出些许人性的关怀,弱者就会感激涕零,这种感恩戴德的土壤中自然不乏爱的种子,一旦时机成熟,这种爱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意大利影片《夜间守门人》中。身处奥斯维新集中营中的无辜少女不由自主地爱上凶悍而又英俊的纳粹军官,《色戒》中去暗杀汉奸的女特工情不自禁放走在床上跟她翻云覆雨的汉奸头子,都是这种微妙心理暗示下的结果。
正所谓,脚上淌着血,脸上带着笑,心里越痛苦,头上越冒泡。这大概就是所谓痛并快乐着吧。我认为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近年流行的野蛮女友现象其实根源都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