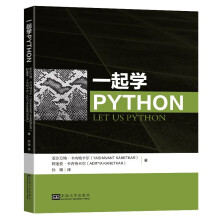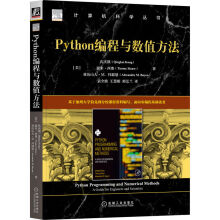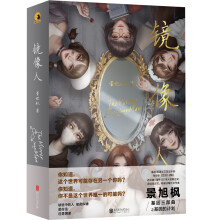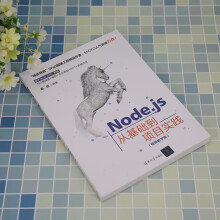木华于春,栗芽于室。
春天来了,栗子树开花了,此时,室内的栗子也开始萌芽。
树木开花和种子萌芽是两件生活中常见的事件,引起古人思考的是:种子早不发芽,晚不发芽,偏偏要等到树木开花时才发芽,而且,今年如此,去年如此,年年如此。
我们现在好理解:生命有节律性,这是遗传决定的。一般情况下,生命的节奏与大自然运动的节奏是同步的,当气温、湿度和光照等环境条件适合时,这种事情就会必然出现,该开花的开花,该萌芽的萌芽。树木开花和种子萌芽是两件互不相关的独立事件,只是栗子树的开花和栗子的发芽这两个事件发生所需要的外部环境条件相近似。
我们的祖先是农民,树木开花好理解:树木种在地里,受土地的滋润,长在野外,阳光雨露之下,当春天来到之时,树木自然就能够开花。如果水、肥充足就会长得好,这样花就多些,果实也结得好些。如果土质差些,水、肥不足,就长得不好,花就少些,果实也差些,甚至不开花、不结果。
种子萌芽就不好解释了:种子在屋子里,没种在地里,也没日晒雨淋,它怎么会萌芽呢?而且,年复一年,不早不晚,总是发生在树木开花的时候。
终于,古人想通了:种子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是树木的一部分,栗子和栗子树本来就是一体!当室外的树木感受到春天的气息而开花的时候,放置在室内的种子受到树木的感应而发生萌芽。
种在土地上的树木得到大地生气的滋润,可以使得它被放置在室内的种子萌芽。那么,如果埋葬在地下的先辈尸骨也得到大地生气的滋润呢,那活着的后人不就发了吗!这便是古人十分朴素的想法。
古人认为,人的身体是父母所生,葬于地下的先辈尸骨和活着的后人的关系就像树木和种子的关系一样,只要让尸骨像树木一样感受到大地之灵气,活着的后人也能像种子一样有所感应,能得到好的命运而兴旺发达,这就是风水所说的:“气感而应,鬼福及人。”(《郭璞古本葬经》)
古人是朴实、天真的!其初衷并不是迷信。
动物不会埋葬死去的同类,埋葬死者是我们人类独有的行为,这是早期人类文明的一种体现。
考古发现,在七千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葬人只是挖个坑,放进尸体,然后盖上土,这就是墓。
“墓,慕也。”(《释名》)慕,就是思念。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
南宋时期的陆游写这首诗的时候_点都不迷信。他告诉他的儿子,他为没有亲眼看到祖国的统一而感到悲伤。朝廷的军队收复北方的那一天,在家祭的时候,不要忘记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我”。
既然是“万事空”了,为什么还要“家祭”呢?虽然死后与人世间无关了,祭祀祖先还是必须的,这是对祖先的追思。
几千年来,埋葬先人的行为经历了由简到繁的演变过程。到大汶口文化(前6300-前4500)的中晚期,以木材为器皿装尸体,我们叫这器皿为“棺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古人“种”下棺材当然是希望得到官和财。古人埋葬下的不仅是先人的骸骨,也埋下了对逝者的思念,埋下了活着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根据“树木的开花和其种子的发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类比、引伸出“埋葬先人的骸骨能福荫后人”,显然并无必然的逻辑性,更不可能以实验来证明。也许,会有某些有成就之人,其祖坟确实符合风水的要求,但仅仅是个案,并无普遍的意义,不可能以现代的统计学知识加以验证。
祈求通过埋葬先人而能福荫后人是迷信的思想,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把生产实践和生存的经验融入到这种迷信的思想中,进而提炼出各式各样的经验和理论,而这些混合着迷信思想、生存经验和生命本能的理论一直指导和规范着后人在择地、建屋、聚居和筑城等方面的行为。
巧合的是,这种带着迷信思想的理论,如果剔除其迷信的部分,剩余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与现代环境科学等现代文明是一致的,区别的只是研究思路的差异和文字表达方式的不同。也正是这种差异,风水可以弥补现代文明的某些空白和不足!
“葬者,乘生气也。”埋葬先人的骸骨,就是要乘大地的生气。
这是《郭璞古本葬经》开头的第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除去“者”和“也”就四个字:葬乘生气。
这四个字是中国风水学说的理论基础,风水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围绕这四个字展开,并不是“座北朝南”、“背山面水”这些生活经验,更加不是“阴阳相济”、“五行生克”、“属猪属狗”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无论阴宅还是阳宅,判别风水的好与坏,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乘大地的生气。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