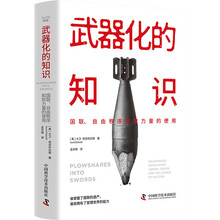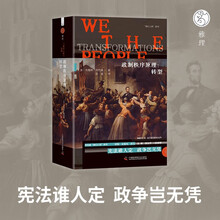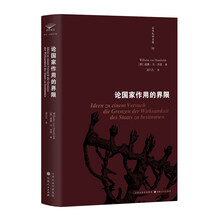在实践上,进入斯图亚特王朝后,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不再单纯局限于中世纪关于“王在法下”,还是“王在法上”的争论,而是要争取法律下的自由,同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中世纪的议会和国王这两个机制的平衡,而是要限制国王的权力,明确宣称议会的权力高于国王的权力,从而为英国人法律下自由的建立奠定基本条件。1641年议会的立法废除了特别容易受到王权控制的法庭和委员会,如星座法庭、高等委员会、债权法庭、地方委员会以及北方委员会和威尔士边区委员会等,从根本上削弱了王权,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取得了永久性的成就,尤其是星座法庭的废除。由于“星座法庭是一个由强制实施一项政策的政客组成的法庭,而不是一个由适用法律的法官组成的法庭”,①它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国王为非的工具和国王专制的象征。在此后的论证中,防止政府的专断行为日益成为核心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一项行动是否属于专断,并不取决于此项权力的渊源,而是取决于该项行动是否符合既已存在的一般性的法律原则。当时的看法是,既已存在的法律如果没有规定,就不能进行惩罚,一项法规只具有前涉力,而不具有既往之力,所有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都应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也就是说,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法律为王”,或“法律即王”。
1641年对王权的另一个限制是取消枢密院的司法权,枢密院不再能够监督和指导地方政府的工作。到王政复辟时,查理二世不仅在中央层面开始受到议会的限制,而且在地方层面也受到地方乡绅的限制,政府的权力比任何时候更加依靠地方团体的支持。到17世纪60年代,除关税外,英国所有的税收、教会立法如信仰划一法、集会法和五英里法以及大部分安全事务,都委托乡绅阶级出身的地方法官,不再需要诉诸中央宫廷的决定。这种权力的下移进一步限制了王权,确立了普通法法庭的权威。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繁琐的、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顽强地抵制住来自上级的进攻。大致从这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来保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同时,法官相对于国王的独立性也得到了强化,法官现在可以坚持其操守(他们只有在犯罪而被宣布有罪或经过上下两院批准的情况下才能被解职),而不必取悦于国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