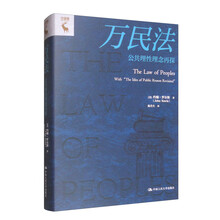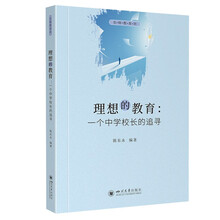偶尔,我们也会把他们拉回到我们初始的研究领域,但主要会是让他们谈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或许就是可以称为“村庄政治生活”或者“草根干群关系”的问题吧。我们不使用强制性的选择题;事实上,我们也放弃了很多我们本来想问但却没有主题限定的问题。对这个崭新的、完全没有预期到的话题,我们也没有利用正式的编码系统,来解读他们的言论的意义。我们甚至也没有想过,去询问一下其他村庄有关“星”的事情。这是这个地方的故事,这是这里的访谈对象热心且具体关注的事情,而我们则很高兴了解了他们所说的故事。之后我们也愿意去弄明白,他们的言论是如何跟我们的研究项目产生关联的;当然,更好的情形是,我们更愿去认真地琢磨一下这些访谈,进一步考虑,是否需要修改我们现在的研究项目(以及一系列我们正在谨慎使用的概念与理论),以便于能够把来自这个村庄的洞察和创见整合进来。
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研究焦点,也没有搜寻新的概念或理论来秩序化我们的发现(在更宽泛的背景下进行的,有关“十星家庭”的比较与分类,参见Thogersen2000:138-40)。但是同样是在那个夏天,我们在山东其他地方以及湖北的实地工作,却真的把我们引向了从未预料到的方向。一些干部提到,在跟刁民或钉子户打交道时总会遇到很多问题。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也有一部分人,他们也根据村民是不是讲理,把村民分成了两类。访谈开始之前,我们没有想到去开发出乡村抗议者的类型学体系,但是很快,我们觉得这个项目比原来的调查目标要更有意思(我们搜集的证据也更支持这样的研究);而那时,我们原来的调查目标是:为增加村庄稳定性而设计出来的选举改革,实际上是不是降低了这种稳定性。
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的学者,把这种中途修正称为“交互式调整”(Gerring2001:231)或者“连续性定义”(Kaplan1964:77)。这就意味着,在开展研究(在我们的案例中,主要是通过访谈的方式)的过程中,研究人员探索的主题以及用来理解这一主题的概念或理论,是不断演化的。在这种解释性的研究工作中,“行”先于“知”(Jones1974)。理论和证据先是紧密纠缠在一起,同时,在研究结束之时,理论、概念与证据是整齐排列在一起,并相互支持的(Gerring2001:231;也见Deanetal.1969:22-23)。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