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尔?斯利兹觉得她老是在往下掉。也正因为她老觉得自己在往下掉,所以她会摔跤。当她站起来,没什么东西支撑时,就那么一会儿,她看上去就像站在悬崖边上一样,不小心就要栽下去。她开始向一侧倾斜、晃动头部,并且伸出手臂力图让自己稳住。不久,她整个人都像筛糠一样浑身震颤,看上去就像一个走钢丝的人,在失去平衡前的那一瞬间,身肢剧烈地俯仰、扭动——只有她的双脚劈开,牢牢地扎在地上。她似乎不单单害怕掉下去,而更怕的是被人推下去。“你就像一个摇摇晃晃走在桥上的人一样”,我说。
“是的,我觉得我会跳下去,尽管我不想这样做。”
通过更进一步的观察,我发现当她试图站稳的时候,她就会浑身抽搐,好像有一伙看不见的恶棍将她推来搡去,要把她击倒在地一样。实则这伙恶魔就在她内心里头,如此不断地折磨她已达五年之久。如果她想要走一走,就不得不扶着墙。即便这样,她还是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样,走起来摇摇晃晃。
对谢丽尔来说,她内心得不到片刻的安宁,即便是她倒在地板上的时候。
“当你已经倒在地面上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问她。“是不是那种要倒下去的念头就立刻消失了呢?”
“有那么几回”,谢里说,“当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地板的存在的时候……一扇想象的地板门豁然打开将我吞了进去。”即使当她倒在地上的时候,她还是感觉她仍然在往下掉,永远地往下掉,直至落入无底的深渊中。
谢丽尔的问题在于她的前庭器,也即平衡系统的传感器官失灵了。她为此活得很累,并且她心头那种总是往下坠落的感觉快把她逼疯了,这种感觉挥之不去,让她无法再考虑任何别的事情。她害怕未来。她出问题后,不久就丢了作为一名国际营销代表的工作,现在只靠每月1000美元的残疾人抚恤金生活。她现在又有一种新的恐惧,就是害怕变老。而且她还有一种罕见的莫名的焦虑。
具备功能正常的平衡感是保证我们安康幸福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平时少有人提及,但却又至关重要。早在20世纪30年代精神病学家保罗?希尔德就研究了人类健康的官能和“平稳的”体像是如何跟前庭器相关联的。当我们谈到“觉得安定”或者“不安定”;“平衡的”或者“失衡的”;“生根的”或者“无根的”;“落地的”或者“悬空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在使用一种前庭语言。这种语言的真相只有像谢丽尔那样的人才能够完全体会。丝毫也不令人奇怪的是,像她那样有相同病症的人常常精神崩溃,而且其中许多人选择了自杀。
我们具有的许多官能,在失去之后,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平衡感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它运行得是如此完美,如此天衣无缝,以致它在亚里士多德所描述过的五种官能里难觅芳踪,自此之后世世代代无人提及。
平衡系统带给我们空间方位感。前庭器,也即平衡系统的感觉器官是由内耳的三个半规管组成的,它们通过探测三维空间中的位移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是站立的,重力是如何作用于我们身体的。其中一个半规管探测水平方向的位移,另一个探测垂直方向的位移,还有一个探测我们或前或后的位移。半规管的管道里头包含了一些纤细的毛细胞。当我们移动头部时,管道里的流体就刺激毛细胞,给大脑发出信号,告诉我们在某一特定的方向上我们提高了速率。每一次运动都要求身体的其余部分作出相应的调整。如果我们向前移动头部,大脑即通知身体的适当部位下意识地作出调整,以便补偿重心的变化,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平衡。从前庭器发出的信号沿着一根神经传到我们大脑中一个特殊的神经元丛中,我们称之为“前庭神经核”。信号在这里得到处理,然后它向肌肉组织发出调整指令。健康的前庭器也跟我们的视觉系统具有紧密的联系。设想你在追赶一辆公共汽车,你向前跑动的同时你的头部也随着在上下起落,你之所以还能将移动的公共汽车保持在你的视野之中,是因为你的前庭器能向大脑发送信息,告诉大脑你跑动的速度和方向。这些信号提供给你的大脑,让它去旋转和校准你眼球的位置,直至瞄准你的目标——那辆公共汽车。
1997年在一次常规子宫切除手术之后,当时三十九岁的谢丽尔,术后受到了感染,于是医生给她开了消炎的庆大霉素。大家都知道过量使用庆大霉素会毒害内耳构造,造成失聪(谢丽尔没有这个症状)、耳鸣(她有这个问题)以及平衡系统的破坏。但是由于庆大霉素价格低廉且易于见效,所以医生仍会开这种药,不过只能使用较短的时间而已。谢丽尔说给她开出的药量超过了限度,于是这样她也就成了庆大霉素受害者这个小小群体中的一员,他们相互之间称为摇摆人。
突然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没法站起来了。她只要动动脑袋,整个房间好像也要动起来。
她闹不清究竟是自己还是墙壁在导致晃动。后来她终于贴紧墙壁勉强站起来,伸手抓来话机给她的医生拨了电话。
她到了医院之后,医生给她做了各种测试来观察她的前庭功能是否丧失。他们让她头靠在一张桌子上,往她耳朵里又是灌凉水又是灌温水。他们要她闭上眼睛站起来时,结果她一下子就跌倒了。一位医生告诉她,“你没有平衡功能了”。测试结果表明她大约只剩了2%的功能。
她说,“医生是这样的冷漠无情,‘这似乎是庆大霉素的毒副作用。’”说到这里谢丽尔激动起来。“到底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些?‘这是永久性的了’,他说。我于是一个人躲起来。我母亲带我再去找医生,但她却托词去取车只在医院外边等着我。我母亲问我,‘能好起来吗’?我看着她,说,‘是永久性的了……再也摆脱不了了’”。
因为谢丽尔的前庭器和她的视觉系统之间的连接受损,她的眼睛不能动自如地跟踪移动的目标。“我看到的一切东西都像业余级的蹩脚录像一样上下跳动”,她说道,“好像所有我看见的东西都是吉露果冻做的,而且我每踏出一步,所有东西也随着晃动起来”。
虽然她不能用眼睛追踪移动的物体了,但眼睛依然是她知道自己站立的最后依靠。它通过对水平线的确定,能帮助人们知道自己在空间中所处的位置。只要灯一灭,谢丽尔立刻就摔倒在地。可视觉辅助最终还是被证实对她来说并不可靠,因为在她面前任何形式的移动——甚至别人伸手去扶她——都会刺激她的坠落感。甚至地毯上的之字形花纹也能让她摔跟斗,冷不丁看到这些花纹她会错以为自己也是像之字形那样歪歪扭扭地站着,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她长期处于精神疲惫,高度紧张之中。为了保持站立的姿势花去了她大量的脑力,本来可用在像记忆和计算、推理能力等这样的心智功能上的脑力。
在尤里为谢丽尔准备计算机时,他们叫我也来试试那台机器。我便戴上那顶安全帽,并往嘴里搁进那个带电极的塑料装置,叫做舌面显示器。它扁扁的,不会比一片口香糖厚。
那个帽子里头的加速计,或者说传感器,可以探测两个平面上的位移。当我点点头的时候,这个动作就被转化到计算机屏幕上的一幅图谱上,研究人员就能对之进行监控。同样这幅图谱也投射在了144个电极的阵列上,这个阵列被植入到了搁在我舌头上的塑料条里了。当我向前倾时,好像香槟酒气泡那样的电震就在我的舌叶上破裂开来,从而告诉我我正在向前弯腰。在计算机屏幕上我能看见我头部的位置。当我向后仰时,我能感觉到舌根处像有香槟酒的涡流在微微波动。我向左右两侧倾斜时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随后我闭上眼睛,练
习用舌头去感觉自己在空间中的姿态。过了不久我就能准确知道我在空间中所处的位置,而且很快忘了传感信息是来自于我的舌头了。
谢丽尔取回这顶帽子;她靠在桌子上来保持身体平衡。
“我们开始吧”,尤里边说边调整着各种控制按钮。
谢丽尔戴上帽子并闭上了眼睛。她从桌子上支起身来,只留两个指头和桌面保持接触。尽管除了舌头上的“香槟酒涡流”之外,并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告诉她哪儿是上哪儿是下,这回她可没再摔倒了。她的手指从桌子上挪开了。从此她不再摇晃。她开始大哭——遭受创伤之后的泪水像洪水一样涌出;既然她戴上了那顶帽子并且感到保险,她就可以轻松一下了。当她一戴上那顶帽子,那种老是往下掉的感觉就离她而去了——五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她今天的目标是不用任何支撑,站立二十分钟,戴着那顶帽子,设法保持住平衡。但对任何人来
说——更别提摇摆人了——笔直站立二十分钟可能都得有白金汉宫门卫那样的训练和技巧。
她看上去很平静,只是稍稍调整了一下站姿。她不再浑身抽搐,那个好像在内心里头将她推来搡去的神秘恶魔消失了。大脑把仿真前庭器传来的信号进行了解码。对她来说,片刻的安宁都是奇迹——神经塑性的奇迹,因为这些舌头上麻麻的感觉竟然莫名其妙地经过大脑中一条新的通道,送到了处理平衡的脑区中。而正常情况下它们是要送到大脑中称为感觉皮层的部分——就是大脑表面处理触觉的一个薄层中去的。
“我们正在想办法把这个装置做得足够小,到时可以藏在嘴里头”,巴赫-伊-里塔说道,“就像矫正牙齿的牙套那样。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么她,和任何其他有这个问题的人,都将恢复正常的生活。像谢丽尔这样的人都能戴着这种仪器,说话,吃饭,而任何人都不会有所察觉”。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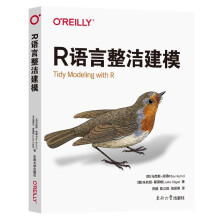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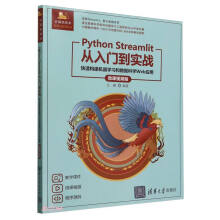


──奧利佛?萨克斯(Oliver Sacks),《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作者
多年来神经科学家一直认为,大脑是一个机器:部分遭破坏,就永远失去這部分的功能。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即使是面临灾难性创伤,大脑仍可以自行修复,增强大脑功能一如锻炼软弱的肌肉。本书是一个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教的精神科医师和心理分析师,访谈研究大脑如何改变的科学家及被他们改造的病人,所写下有趣迷人而且不曾被正确理解的奇迹故事。
──《出版家周刊》(Publishers Weekly)
脑科学领域中最新的专业术语应该就属于“神经可塑性”了,这个概念显示成人的脑仍有改进的可能性。夏伦?贝格利(Sharon Begley)的《训练你的心灵、改变你的大脑》(Train Your Mind , Change Your Brain)虽然也是相同主题的著作,不过道伊奇医师在本书中描述这些因神经可塑性而得救,或是接受相关训练而改善能力的故事,对于非专业領域的一般读者应该更具吸引力。
──《图书馆学刊》(Library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