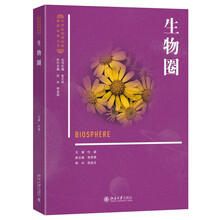第一章“道”的技术哲学意蕴
“道”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内涵极丰富的基本范畴,“道”与“技”的关系是“道”的理论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这个方面与“道”的其他方面内涵有着本质上的内在联系。从技术哲学角度对“道”加以诠释,不仅有助于对“道”“技”关系的理解,还可以使古代典籍中关于“道”的不少看似神秘费解的论述得到新的合理解释。“道”的技术哲学意蕴具有三个层面含义:从本体论层面看,“道”是“技”的理想境界;从认识论层面看,由“技”至“道”的发展要靠直观体悟;从方法论层面看,“道”对“技”的引导体现为贯彻一系列具有辩证思维特征的准则。这三个层面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是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的理论基础。
一、“道”——“技”的理想境界
“道”是不能直接从逻辑角度下定义的,“道”与“技”的关系有着远远超出逻辑关系的丰富意蕴。从技术活动角度看,“道”是“技”的理想境界。这不是下定义,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诠释或说明。“道”“技”关系是对人类技术活动本质特征的深刻反映,这一点也需要通过逐步深入的诠释才能理解清楚。
1.“道”的原型和本意
“道”的最初含意就是人们熟悉的“道路”。许慎的《说文解字》对“道”的解释是“从行从首,一达谓之道”。据考证,“道”的象形字上为一个“首”(象征一个人),朝着道路上的某处走(即上为“首”下为“走”)。这意味着“道”与“路”其实有所区别。“路”是实物形态的东西,如泥土路、石板路或柏油路,即使在无人走时也是实际存在的。而“道”更多表示的是道路的功能,即能够使人们在头脑支配下由此处走向彼处,这与走路者的需求和动作直接相关。人在“道”上要一步一步走,这里蕴含着行走的目的、方向、步骤。人们的其他各种实践活动其实都具有类似的特点,即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再做什么。正因为有这种往往并非自觉的人生体验,人们谈到各种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方法时,也常借用“道”的最初含义,使用“通过”、“途径”、“步骤”、“走向”等词汇。与此类似,英语中的“Way”既有“道路”的含义,也有“途径、方法”的含义,同样体现了这一特征。
然而,作为中国哲学范畴的“道”,并非指实在的道路或道路上实际的行走过程,也不限于各种实践活动中具体的途径和方法。在我国古代,各种具体的途径或方法被称为“技”或“术”,而不是“道”。老子强调“道”本身无具体形象,不可言说,这意味着不仅把人们对实在道路的体验抽象掉了,而且把各种具体途径和方法的特性也抽象掉了,留下的只是对于应“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再做什么”这种步骤性活动自身的本质特征的体验。就人类的技术实践而言,这种本质特征指的是:任何技术活动都由一系列前后衔接、首尾相连的步骤或环节组成。各种具体的途径和方法,都是对一系列步骤或环节上操作者、工具、对象等技术要素相互关系的具体规定(这里所谓“途径”,涉及各步骤或环节之间的关系;而“方法”则涉及每一步骤或环节上操作者、工具、对象等技术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些途径和方法对操作者而言当然是人为的,而且不同的操作者可能采用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其成效也不尽相同。但根据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等技术要素的自然本性,应该存在一种合理的、最优的途径和方法,这实际上就是“技”之上的“道”。
“道”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是由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等相关技术要素的自然本性共同决定的。它超越了各种具体的“技”,是“技”的理想境界。庖丁解牛注重牛的筋骨皮肉的生理特征,下刀都在游刃有余之处,不仅省力省时、干净利落,而且不磨损刀具,这就是既合乎操作者自然本性,又合乎工具自然本性,还合乎技术对象自然本性的途径和方法,这就达到了“道”的境界。追求“技”之上的“道”,目的在于使人为设定的途径和方法逐步转化为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途径和方法,以至于达到能运用自如、天人合一的程度,因而老子才强调“道法自然”。
需要特别指出,这里关于“道”的所谓“合理的、最优的”要求,有其特定含义。“合理”的要求是从技术活动相关要素的关系着眼,注重由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的自然本性共同决定的客观特性,这种客观特性具体表现为技术活动相关要素之间的和谐。“最优”的要求,是从技术活动的社会价值和效益着眼,注重技术活动主体的需求和感受,具体表现为省力、优质、高效,有一种成就感。“庖丁解牛”的寓言中体现出来的“道”,显然既是合理的,又是最优的。合理的途径和方法决定了最优的效果,而对最优目标的追求引导了对合理途径和方法的不断揭示。关于技术活动的合理、最优、和谐的要求,无论在古代技术中还是近现代技术中,都是普遍适用的,这里体现了“道”的普适价值。
还应注意,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是有形的,而“道”是无形的。“道”并不是具体的操作者、工具和对象,也不是操作者的实际动作,而是合理的、最优的途径和方法本身。它实际上是一种师法自然的特定“程序”。这里使用“程序”一词,应该说是一种隐喻,用以说明“道”是由前后相继的步骤或环节组成的特定路径,其价值在于特定的路径选择和步骤或环节的特定组成方式,在这一点上同现代意义上的“程序”概念有共同之处。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程序”概念也强调特定的路径的选择和步骤或环节的特定组成方式(即所谓“路径依赖性”),以这种无形的方式体现其价值,即所谓“软件”的价值。
不过,“道”的程序性活动特征与现代的“程序”概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现在人们通常理解的程序,是计算机上人工编制的程序,还有程控机床上按指令操作的程序,以及会议程序、操练程序、仪式程序等等,概言之,都是人工设定的程序。这些程序的编制和设定本身属于“技”的层面。尽管其中也有是否合乎事物自然本性,是否合理、最优的要求,但这些人工设定的程序本身已经在实用层面上独立发挥作用,成为现代软件产业的基础。严格的“程序”概念来自控制理论和计算机科学,这是将近现代技术活动的程序特性单独抽象出来加以研究、设计和广泛应用的结果,是对人工设定程序的专业化对象性研究。我国古代先哲当然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程序”意识。他们对“道”的理解,只能是把握类似于今天“程序”概念的某些特性,即本身无具体形象,与途径和方法相关,前后相继,首尾衔接等等。如老子所说“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或如管子学派所述:“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可是,他们能够将对程序性活动的体验从对实在的道路体验中分离出来,而且对“道”的理解具有远远超出人工设定程序的广泛而深刻的意义,这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成就。
关于“道”的这种技术哲学意蕴的诠释,可能会引起某些疑问或误解,这里需要做一些说明。
首先,这里运用现代的学术语言,将“道”解读为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合理的、最优的途径和方法,或者说看作是一种师法自然的特定“程序”,是否符合老子、庄子、管子等古代先哲的本意?换言之,这是不是站在今人角度对先人观念的一种曲解?对这种疑问的回答是:的确,老子、庄子、管子等古代先哲都没有这种明确的表述,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一系列论述中做出这样的合理推断。
庄子的寓言“庖丁解牛”,在表述这种含义方面应该说是最典型的了。类似的还有庄子对“道”的论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显然,如果“道”与途径、方法无关,当然也就无所谓“传”“受”的问题。然而老子的相关表述比较隐蔽,需要仔细加以分辨。比如老子认为“道”可执(“执大象,天下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可为规则、程式(“是以圣人执一为天下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这其实正是在强调“道”作为途径和方法的功能。老子的论述有时还直接用到“道路”的比喻,如“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其人好径”等等,这似乎更显示了对“道”的本意的体验。
老子对“道法自然”的反复强调,反映出对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要求的高度重视。至于对合理性和最优化的考虑,老子的表述则更为隐蔽。比如老子讲“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其意是说,“道”之所用,就在于利用事物按照自然本性发展的态势,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实现尽可能多的收益,获得最优的效果,这就是所谓“因势利导”。老子还讲过“上善若水”。他之所以对“水”的隐喻特征极感兴趣,正是由于水流能够因势而下、灵活多变,实际上取一条合理而又最优的路径。老子又提到“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自然的程序当然是费力最小的程序。老子强调“无为”,使事物“自化”,实际上包含了对各种实践活动合理性和最优化效果的深刻思考。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