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秦时期西域探险
一、先秦时期西域探险史述
秦朝以前的中原人,有到西域探险的吗?说起来似乎都是神话传说,远古的梦幻,云山雾罩,扑朔迷离,如同天方夜谭,荒诞不经。
然而,事实并不完全如此。远古人类留下的历史,虽然有虚构的成分,但却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有它的历史原型。古人将历史神话化,又将神话历史化,说明二者之间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历史是人的历史,但最早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神话传说。正如英国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所说:“神话是已知事实的一种陈述。”就如三皇五帝之类,也都是从神话人物中剥离出来的历史人物。
所以,只要我们拨开历史迷雾的一条缝隙,仔细辨识,就不难窥视到历史人物的清晰面目,也不难发现远古先民在西域艰难跋涉的印迹遗痕。
黄帝命伶伦作音律于昆仑的故事,就是原始先民远赴西域的最早信息。
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黄帝诏伶伦作为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及之昆仑之阴,取竹于懈溪之谷,以生窍厚薄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之昆仑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制十二律……”
伶伦是黄帝轩辕氏的乐官,伶伦奉黄帝之命制定音律,从中原一直走到昆仑之丘,途中怎样历尽坎坷,饱尝艰辛,那是难以想象的。那时的昆仑山不是冰雪覆盖的群山,而是翠竹遍野、百鸟鸣啭的长春之山。伶伦到达昆仑之丘的懈谷地方,挑选了一些长得薄而均匀的竹子,截去竹节,做了十二支不足四寸的竹笛。他试吹了一下,虽然声音响亮,但无和谐之韵。这时,他听到凤鸟的呜叫,受到启发,就随着凤鸟的叫声,从高到低划分为六个音阶,伶伦反复吹奏,终于创制了十二根律管,制定了我国最早的音律,以后的人们就有了创作演奏音乐的规范和依据了。《吕氏春秋·古乐篇》还记载,黄帝又命伶伦奏乐,“始奏之,命之日成池”。《咸池》本是西天星座的名称,是“天池”的意思,可见《咸池》古乐应与西域的乐舞及天象星座有关。这就把伶伦作乐与昆仑之丘联系在一起。假使传说中的伶伦有历史原型,那这位“伶伦”就不仅是初制音律的伟大音乐家,也应是前无古人的西域探险家。
我国一些古籍记载,尧、舜、禹都与西域有往来关系。如贾谊《新书·修政语》上篇说:“尧日: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见西王母。”《易林》卷一也有:“稷为尧使,西见王母,拜请百福,赐我善子。”《荀子·大略》则进一步说:“尧学于君巂,舜学于成昭,禹学于西王国。”这些圣王的所谓“学”就是到西陲之地游学、巡视。
这些记载,多为传说,不成信史。但至少从中透出一些信息,尧、舜、禹时代就有了中原与西域的某种联系。
屡屡出土的大量文物,为这种联系提供了实证。早在公元前十三世纪,由西域向中原运输玉石的商道“玉石之路”就已形成。《考工记》称,夏、商、周三代都设有专管玉器的“玉府”和专为琢玉的“玉人”,曾不断派人去西域采玉。河南安阳殷墟距今3200年前的殷王武丁之妻妇好墓,出土了756件玉器,包括礼器、仪仗、日用品和装饰品等,不仅数量多,而且玉质晶莹润泽,雕工精美。经专业单位鉴定,确认这批玉器来自新疆,为和田软玉和子玉。江西新干一座商墓出土了150多件玉器及近千件小玉珠、玉管、小玉片等,经鉴定其中就有新疆和田玉,即“昆山之玉”。西安附近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的一批古玉,经中国地质专家研究,其中大部分是从昆仑山采集的和田玉。湖北随县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也出土了一批和田玉器。《史记·赵世家》还记载了战国时期纵横家苏厉在给赵惠文王的上书中说,如果听任秦国出兵赵国,切断横山通路,则“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昆山之玉产于昆仑山北缘一带,胡犬则应产于中亚、西亚地区。此外,新疆一些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历史遗址,出土过许多来自中原地区的漆器、铜镜、丝织品,甚至还有产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海菊贝壳制成的随葬饰珠。无论是玉器的东输,还是中原器物的西进,都是由人来采办和运输的,大量的商道运作绝非轻而易举。万水千山,冰峰雪岭,大漠瀚海,四野荒蛮,无论是王者还是平民,只要迈开了西行的脚步,踏上了未知领域的行程,就担起了风险,就具有了冒险和探险的性质了。只不过,这些涉足西域的先行者,只是一些无名的英雄探险家和旅行家罢了。
周穆王
周穆王西巡的故事,早在《穆天子传》发现之前就已流传于世,且有史载为据。《左传》说他“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而使天下的道路都印上自己的车辙马迹,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旅行家。《史记·秦本记》说,“造父善御,得八骏,穆王使驾而西行巡狩”,穿天山,登昆仑,与西王母会见。《赵世家》又进一步说,“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
周穆王姬满,在他即位的第十三年(公元前989年),以伯夭为向导,乘造父驾的八骏马车,带着大量精美丝织品和中原物产西行。他从王都宗周洛阳出发,从陕西人河南,经山西到内蒙,沿黄河经宁夏至甘肃、青海,进入新疆,登昆仑、上舂山抵赤乌居住之地。《山海经·北山经》载:“过舂之山多葱”,应指葱岭。赤乌在昆仑山北麓,赤乌是周太王古公亶父女婿的后裔,与周宗室同出一系,说明汉族移民已到葱岭,这也许是周穆王远行葱岭的一个历史基础。“赤鸟,美人之地也,瑶玉之所在也。”这一带即是西王母部落和塞人所在地,又是出产瑶玉的地方。周穆王在这群玉之山采取大量玉石,“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运往中原。周穆王继续西行,来到西王母之邦,演绎了一幕瑶池相会,对歌作乐的浪漫故事。最后,周穆王顺黑水(锡尔河)北行到达中亚草原,取道伊犁河谷经天山北路返回中原。
生活在天山一带和中亚西亚的游牧部落是“塞人”,他们是西域最早的居民。祁连山南麓和以西都是塞人祖居之地,后来越迁越远。周穆王西行,大致就是追随着塞人西迁的路线。
周穆王每到一地,都以金银珠宝、丝绢、铜器、贝币馈赠各部落酋长,各地酋长也向他回赠大量牛、马、羊和美酒。开拓了玉石成批东运和中原丝绢、铜器西传的新纪元,西运的货物远远越过葱岭,一直伸向中亚草原、伊朗高原。
周穆王往返行程三万五千里,历时五百四十三天。《穆天子传》所记载的日期、方向、地名、里数以及西域部落、语言、人物、出产、山川、风物等,不能不信其为实录。周穆王与西王母会见虽然是民间传说,但它不仅被写进了《穆天子传》,也被写进了编年体的史书《竹书纪年》。可见,穆天子西域巡狩的故事也并非无本之木,而是后人根据周穆王西征戎狄的史实渲染演化而来。同时,远古人类交往的许多史实,也构成了周穆王西巡传说的历史基础。
穆天子巡游西域,反映了西周强盛时期对西域秘境探寻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原本就“肆欲其心,周行天山”,而使自己的车辙马迹印在天下道路的周穆王,应是西域巡游开先河者,也即西域秘境探险第一人。
自周穆王巡游西域之后,齐桓公又有了一次西征之行。
齐桓公
齐国是春秋时期最先强大起来的诸侯国,齐桓公是一位豁达大度,知人善任的政治家。在“使相”管仲“富国强兵”政策支撑下,齐国一跃而为诸侯的霸主。正如司马迁所说:“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谋也。”《史记·齐太公世家》还说:“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于是齐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这就是齐桓公西征的最初信息。
《国语·齐语》、《管子·小匡》等文献,也都有与《史记》相似的记载。诸如齐桓公即位数年,“一战帅服三十国……遂北伐山戎……西服流沙西吴。”“……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遂南伐楚,傅方域,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等等。
齐桓公西征到达最远的地方,文献记载为“流沙西吴”与“流沙西虞”。“西吴”与“西虞”在哪里?据王守春先生在《齐桓公至新疆试证》(《西域研究》1999年第1期)论证,“西吴”、“西虞”应为一地,在流沙以西的地方。即齐桓公到了黄土高原地区或鄂尔多斯地区后,又西向流沙即河西走廊北面的沙漠。齐桓公到了“流沙”地区后继续西征,进入今天新疆地区。然而,齐桓公到达的西部地区,没有周穆王所到的那么远。周穆王到达伊犁河谷、赛里木湖以及准噶尔盆地最西部,“而齐桓公可能只到了今新疆的东部地区,可能只是到了天山东部的哈密地区或阿尔泰山东部地区。”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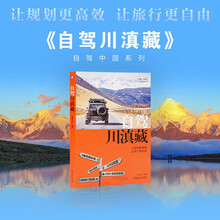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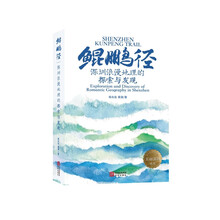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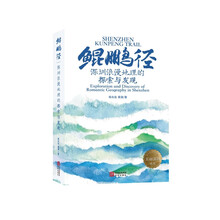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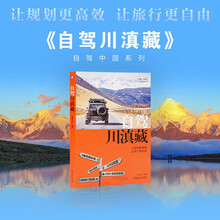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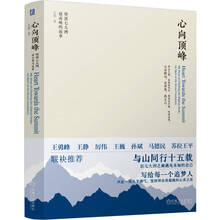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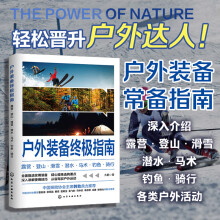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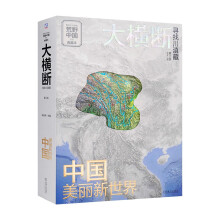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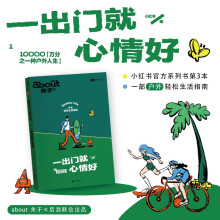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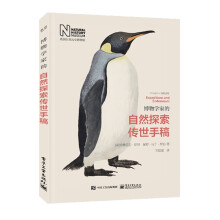

——王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