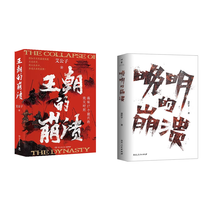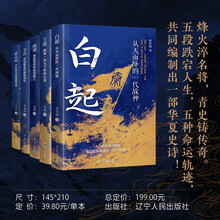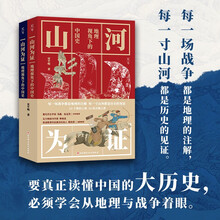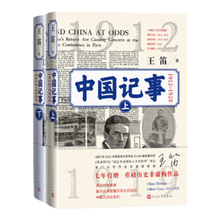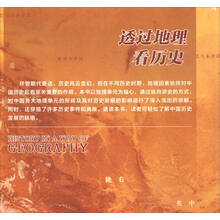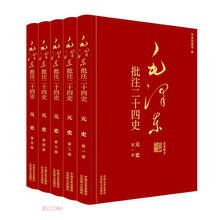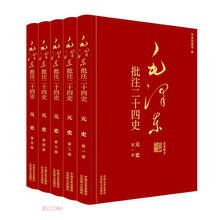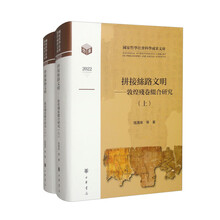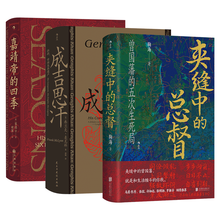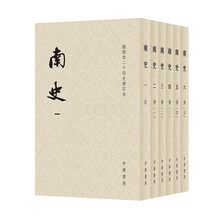都说嘉庆皇帝从乾隆手中接过的是一支沉重的权杖,是掩盖在盛世下的腐朽与危机,事实的确如此。难道嘉庆帝自己就没有丝毫察觉吗?从执政后的所作所为分析,嘉庆帝不仅知道而且用最大的决心和毅力,力图铲除一个个腐蚀、破坏国家和社会肌体的毒瘤。嘉庆帝亲政后最大的问题是想办法缓解经济,于是他终止祖父辈热衷的南巡传统,他固然留恋当年随父皇南巡时看到的江南美景,歌舞升平曾给他带来的愉悦和陶醉,但他更没有忘记乾隆帝说的话:“我当皇帝六十年,自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惟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把好事办成了坏事。”但这仅是冰山一角,从嘉庆帝即位开始清廷用近9年的时间完成了剿捕白莲教战事,调动16个省的兵力,耗银2亿两,这些钱相当于清廷4年的财政收入,虽然清廷艰难地支撑了下来,但对原本就匮乏的清朝财政如同雪上加霜。无奈嘉庆帝冒着违背祖训的大不敬,大搞捐输捐纳,京官自员外郎以下,外官自道、府以下,武官自游击以下均可报捐,这也使一些无才而有财的人混入仕途。随着捐纳之风愈演愈烈,捐官的钱也越要越多,又加速了腐朽之风的盛行。清朝的捐纳就是人们常说的卖官鬻爵。它通常由政府先制定出条例、价格,然后公开出售,慢慢地成为了一种制度。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开捐主要是为了筹集军饷、治河、赈灾的费用,对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秩序的安定曾起了重要作用。到雍正时,捐纳弊窦已凸显出来,那些负责经办捐纳的官员公开“卖官卖法,贪污中饱”。许多捐纳出身的官吏“不能发愤自砺,志趣卑陋,甘于污下,久居民上,荼毒小民”。乾隆年间大量的地主、商人、官僚子弟捐官,“以官为市”,造成“名器日滥…流品杂沓”。不少人捐官到任后,唯以“敛财以补偿之计”,“收受陋规为职事”。而那些捐有官衔的纨祷子弟,更是依“官”仗势,横行不法,商人也以“官”为护符,加重对平民百姓的盘剥。清廷开捐的本意是要把捐纳的钱用于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安定,结果反而刺激了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乾隆帝已看出这些问题,他说:“为治之要首在用人,而人才究以正途为重。前因军需、河务支用浩繁曾暂开捐例,原属一时权宜之计,不久即行停止。”他果断地下令停止捐纳,并要求子孙永远“奉以为法”不再开办。
据清宫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类档案记载,嘉庆年间的捐输是最繁重的,国家每年都要以大量的捐纳用于缓解国家财政之不足。这些钱被用在剿捕起义军、治理河工、军需军备等方面,甚至皇族家事的一些用银也因国库无力支付而使用捐纳。如嘉庆四年(1799)洋商潘致祥、盐商温永裕等请求各捐银20万两以备悬赏平苗立功官兵;嘉庆五年(1800)盐商温永裕、吴叙慈等再一次呈请捐输50万两为平定川陕白莲教用;嘉庆十九年(1814)洋商公捐银24万两、盐商公捐银16万两用于补充军费开支。嘉庆十年(1805)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徽商鲍漱芳先后捐米6万石、麦4万石赈济了数十万灾民,后他又集众输银300万两开山归海。鲍漱芳屡次捐输的行为深得嘉庆皇帝赞赏,这些事例在清宫的人事档案中有大量的记载。对嘉庆帝大搞捐输捐纳,且不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仅就这一做法而言充分表现出他对富国强民的渴望和急于求成的心情。通过各种努力,嘉庆一朝的国政出现了转机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这一切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社会危机,积弊太深及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使嘉庆帝如履薄冰。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