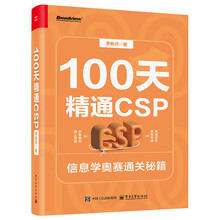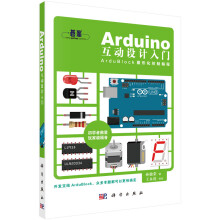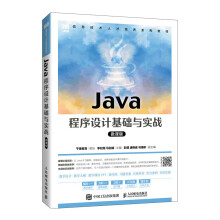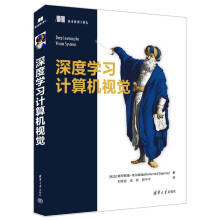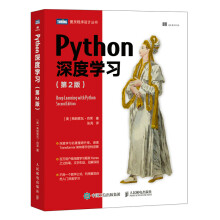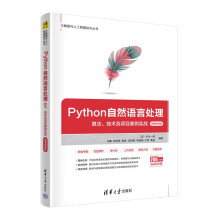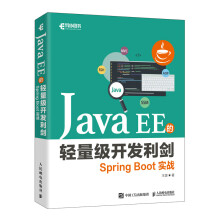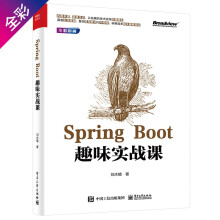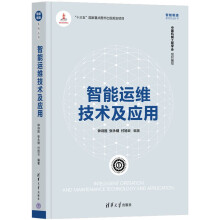整体性比较并不回避选题,如果它要保持可行性的话。一个成功的整体性比较甚至完全取决于选题。这里有四种基本的可能性。第一,整体性比较要以此为方向,即消除关于社会之间差异性的历史偏见或是审视那些未经检验的有关这种差异性的研究课题。首先要面对这类偏见或这类研究项目,然后在这些研究领域中着手进行历史的比较。第二,整体性历史比较要寻求不同社会的内在逻辑,然后选择比较课题,这些选题要能够体现其基本的逻辑关系。最近的例子如埃森斯塔德(S.N.Eisenstadt)对日本的比较史的考察。他首先在同西方的比较中看到日本社会的特殊性,即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同某一革命并非紧密相关,日本对现代性的理解同西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日本历史上不存在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且自上而下调控的国家力量软弱,日本在基本参变量上同西方不同并且遵循另外的发展逻辑。第三,在比较实践中所有这些研究课题都可以选择,即它们对整体性比较是至关重要的,并且要特别注意这样的研究对象,即所比较的社会之间的差异性被特别地塑造出来或者这种差异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第四,总体性比较在选题时也要有理论方向,而且要集中考察理论所认为的基本方面。对此有一个例子是彼得·弗洛拉(Peter Flora)收集的广泛材料,这些材料作为19-20世纪欧洲内部西欧国家之间比较的基础,就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而构建的,并且首先选择的各个时间系列是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劳动力、教育、城市化、劳工冲突、选举和选举人、国家财政和福利国家。
显然在实践中整体性比较是十分少见的。历史比较通常是特殊性比较。占绝对多数的比较并不是关于整体性的,而是关于有特殊目的的某个机构、个别的社会群体、某种结构或心态、个别的事件或进程。特殊性比较之所以有别于整体性或总体性比较,是因为它并不研究社会的所有方面,而只是集中在特殊的课题上面。当然这种特殊性比较也会促进整体性比较,而且特殊性比较首先也要在比较中考察机构、社会群体或事件的一般原则。它还可以比较个性化之间的差异。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