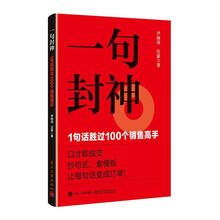《新唐书》对历史的贡献之一是,它的“南蛮传”详细记载了当时和唐帝国有往来的国家。
《新唐书》专为立传的“南海国”有林邑、婆利、罗刹、婆罗、殊奈、盘盘、哥罗、拘蒌蜜、扶南、白头、真腊、参半、道明、诃陵、堕和罗、昙陵、陀洹、堕婆登、投和、瞻博、千支、哥罗舍分、修罗分、甘毕、多摩苌、室利佛逝、名蔑、单单、罗越、骠国30国,提到的国家或地区有奔浪陀、大浦、西屠夷、赤土、丹丹、甘棠、僧高、武令、迦乍、鸠密、狼牙修、婆利、不述、车渠、迦罗合弗、迷黎车、婆岸、干支弗、合跋若、磨腊、婆凤、多隆、萨卢、都诃卢、君那卢、真陀桓、但游、波刺、多罗磨、哥谷罗、堕罗钵底31国。
在以上众多国家和地区中,林邑、真腊、骠国、诃陵、室利佛逝诸国与唐朝交往较多。
林邑在今天越南的中南部,一称占婆,唐德宗至德年间(756-758年)以后,又称环王国。
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林邑就两次“贡方物”,此后双方往来不绝,前后来唐聘问达26次之多。
林邑输往唐朝交换的物品主要有谬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珍珠、沉香及杂宝等,其他还有训象、白象、通天犀、五色鹦鹉、白鹦鹉等唐朝境内较为少见或难得一见的珍稀禽兽。
真腊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它原是扶南属国,贞观初年,吞并了扶南。后来,又分为水、陆二真腊。
陆真腊在今天的老挝多山一带,水真腊则在柬埔寨近水地区。从武德年间(618-626年)开始,真腊向唐朝遣使11次,携来犀牛、驯象等物。
骠国在今天的缅甸地区,与唐朝的交往以“骠国献乐”最为有名。
诃陵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它地处唐帝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海上交通要道,自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先后9次遣使来唐,向唐朝贡献僧祗童、僧耆女、五色鹦鹉、频伽鸟、玳瑁、生犀以及异香名宝等物。
与诃陵一样,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岛东南的大港)在唐代南海交通中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并且常常有唐朝人长时间驻留。义净称:“佛逝廓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不殊。沙门轨仪,悉皆无别。若其唐僧欲向西方为听读者,停斯一二载,习其法式,方进中天,亦是佳也。”在文中,他明确将室利佛逝作为唐朝取经僧人预习天竺“法式”的首选之地。
航海业的进步促进对外贸易的繁荣,而外贸的繁荣则促进唐帝国与外国的进一步交流,在接受这些国家的朝贡的同时,唐帝国也彻底开放了自己的市场,这样各个国家和唐帝国之间的往来就更加密切了。在唐代,中国沿海兴起了登州、扬州、明州、泉州和广州等一批以对外贸易为特点的沿海港口城市。
在这些城市中,广州格外引人注目。阿拉伯地理著作《道里邦国志》就以广州为南海诸国航海东方的终点,并称广州港为“中国最大的港口”。
唐人形容广州“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形象地说明了其在唐代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著名诗人杜甫“海胡舶千艘”的诗句更说明,当时广州外商云集。
唐人李肇称广州每年都有“南海舶”——即外国商船停泊。在南海舶中,师子国舶最大,这些船高达数丈,人们上下时都需要搭设梯子,船上堆满了宝货。每当南海舶到来时,“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
商船上都饲养了信鸽,万一在海上遇难,信鸽可以在千里之外归来报信。广州的对外贸易盛极一时,其“利兼水陆,瑰宝山积”,是唐朝宫廷内外所渴求的外来珍奇货物最重要的来源。
长庆三年(823年),郑权赴广州任岭南节度使,韩愈在送别的文章中说,广州是“……蛮胡贾人,舶交海中,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镇……”韩愈显然希望郑权贵而能贫、为仁不富,但郑权在任不满一年,就因贪婪赃污、搜刮奇珍而成为国家的蛀虫。
封建帝国的“盛世”往往意味着官僚的腐化和堕落,中国陶瓷的出口贸易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贪渎”这个烙印。或者因为和韩愈的关系,郑权的堕落才惹人注意——但事实上,在广州“蛮舶之利”的诱惑下,官员贪污已经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唐代广州的各级地方官员中,因贪污贿赂犯罪或因此而致富者,就有党仁弘、萧龄之、周利贞、路元睿、刘巨鳞、彭果、张万顷、徐浩、路嗣恭、王锷、郑权、胡证、王茂元等人。
不少官员的贪污行为是令人发指的,广州都督路元睿掠取“昆仑舶”珍货而遭到外商的刺杀,路嗣恭借口外商违法而“株戮舶商,没其财数百万私有之”。
王锷任岭南节度使时,“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
地方官的贪污行为对广州的对外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769年,李勉前往广州赴任,当时一年才有四五艘西域商船到广州,可见唐代宗时,到了8世纪末,广州对外贸易更是严重衰落,贸易额锐减,甚至无法满足朝廷的需求。当皇帝询问这个情况时,陆贽尖锐指出:“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怀失所。”他明确将海外贸易的衰落归于“侵刻过深”。
而“广州渗案”对海外贸易近于毁灭性的打击却远甚于官员的腐化和盘剥。黄巢造反后,迅速攻占了广州,而这时,广州城内聚居着大批从外国前来唐朝经商的侨民。黄巢就下令屠杀城内居民,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12万人之多。这4种宗教徒的死亡人数所以能知道得这样确凿,是因为中国人按他们的人(头)数课税的缘故。
死亡的外国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聚居广州会有这样的结局,此前因为帝国的盘剥,已经有人决定要离开中国了,但由于是聚居的形式,他们在同一个地区保持着同样的生活习俗,而且还可以推举自己信赖的外国人来担任首领,这样的话,熟悉了环境的外国人在回国问题上就显得非常彷徨——他们寄希望于帝国整治当地官僚,让他们重新生活在“盛世”里,但他们等来了来势迅猛的农民革命和自己的悲惨命运。
谁也不知道黄巢的伟大抱负究竟是什么,沿海地区的贸易城市不断遭到他领导的军队的破坏,“广州惨案”的血还没干,他的军队已经开始勇猛地攻击福建。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