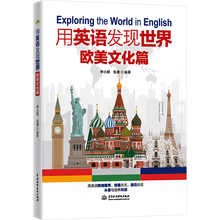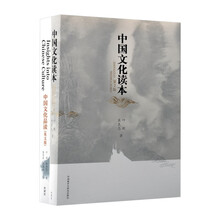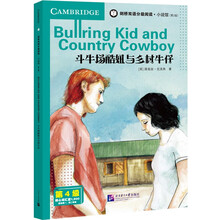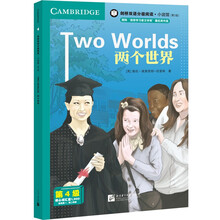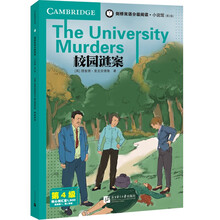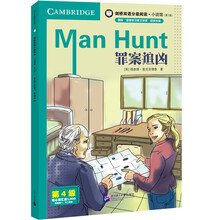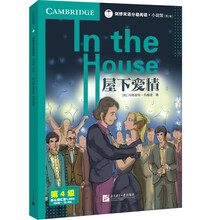第一章 图尔
我羞于从把都兰省说成法国的花园开始,这种说法早就过时了。然而,图尔镇倒还有些甜蜜、明亮的东西,暗示着它是被一片果实累累的土地所环绕。这是个非常怡人的小城,很少有这么大的城镇能比它更丰饶、更完整,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更自得其乐,不嫉妒大地方的那些责任。它不愧是那个好客省份的首府,一个富饶、优裕、友好、舒适、乐观、懒洋洋的地区。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中说过,真正的都兰人是不会费力气,甚至动动地方去寻找乐趣的。不难理解这种和蔼可亲的犬儒主义的来源。都兰人一定模糊地认为,任何变动都只能导致丧失。命运对他们一直仁慈有加:他们生活在有节制的、理性的、好交际的氛围中,他们筑居在一条河的两岸,有时洪水淹没了周围的乡野,但是其破坏似乎如此容易挽回,以致洪水的侵害会被认为(在一个好事不断的地区)仅仅是造成对健康的悬念的一次偶然事件。都兰人有着优良的古老传统,宗教的、社会的、建筑的、烹饪的;他们可能会为自己是地道的法国人而感到一种满足。他们那令人称羡的国家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具有民族特色的了。诺曼底是诺曼底,勃艮第是勃艮第,普罗旺斯是普罗旺斯;但是都兰本质上就是法国。它是诞生了拉伯雷、迪卡尔、巴尔扎克的土地,是好书良朋之乡,而且还有美味佳肴和华丽的屋舍。乔治?桑在某段迷人的文字中说到过法国中部的自然条件的温和方便——“它的气候温暖宜人,雨量充沛,下雨的时间很短。”1882年的秋天,下雨的时间不算短,雨量也更加充沛;但是当天清气朗之时,它的天气可能是再迷人不过的了。葡萄园和果园在清新、快乐的光线中显得丰美无比;到处都在耕作,但到处都显出轻松愉快的景象,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贫困;节俭和成功是良好品位的表现。妇女的白帽子在阳光中闪耀,她们做工精良的木底鞋在坚硬、干净的道路上快乐地喀哒作响。都兰是古堡之乡——有大量的建筑样板和大批的古老遗物。农民们没有法国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农民那样阔绰:但是他们也拥有一定的财产,这赋予了他们精神上少许的保守,在市镇的小交易场上,外乡人往往可以从他们那农用衬衫的棕色褶皱上看出来。而且,这里也是法国君主政体的核心:因为那种君主政体过去的光辉灿烂,其辉煌倒影仍在卢瓦尔河中熠熠闪耀。法国历史上最为震惊人心的事件中有大部分是在那条河的河岸上发生的,它所浇灌的土地曾经盛开过文艺复兴之花。卢瓦尔河给这片风景赋予了一种伟大的“风格”,而风景的特色却没有“风格”那么突出;这条河把人的目光带往比都兰绿色的地平线更有诗意的远方。它是一条时断时续的激流,有时水流很浅,可以看见粗糙的河床——这当然是河流的一大缺陷,因为它所浇灌的地带是如此依赖它所带来的那种气派。但是我要说说我最近一次看到它的情景:满溢、宁静、有力,缓慢地弯曲成弧形,折射出半边天光。再没有比你从昂布瓦斯城垛和露台上看见的河流景色更为美丽的了。一个怡人的星期天早晨,当我从那个高度向下俯瞰时,透过柔和闪烁的秋日的阳光,卢瓦尔河似乎就是一条慷慨仁慈的河流的楷模。图尔最为迷人的部分自然是俯瞰卢瓦尔河的林阴码头了,它隔河远眺圣桑福里安友好的郊区和那里耸立着的台地。确实,在整个都兰省,你可以沿河旅行,体会它一半的魅力。大堤保护着它,或者说是保护着乡野免遭河水的侵害,从布卢瓦到昂热一侧是一条令人叹为观止的大路;同样,在另一侧,有高速公路一直与之为伴。当你循着一条大路旅行时,一条大河是出色的旅伴;它缩短了行程。
图尔的旅馆大多位于另一个地段,其中一家,正好在城镇和车站的中途,条件非常好。值得一提的是,旅馆里的每个人都非常礼貌殷勤——这种殷勤不自然到一开始会激起你的怀疑,以为旅馆有什么隐藏的罪恶,所以男女服务员们才事先试图让你安下心来。尤其是有一个侍者,他是我所遇见的最擅长社交的人,整天从早到晚喃喃着一些客套话,像陀螺一样嗡嗡着。我要补充的是,在“世界旅馆”没有发现什么暗中的秘密:因为在一间闷热的房间里吃温吞的晚餐,是一种令人生厌的义务,也是纯属无奈,但对今天的旅行者来说,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另外,在图尔,有一条气派不凡的“国王街”,是一百年前建造的,上面的房屋都是一个模样,中等规模,具有18世纪自命不凡的外观。这条街把城镇中最重要的非宗教建筑——法院——和横跨卢瓦尔河的大桥连接起来。巴尔扎克在《图尔的本堂神甫》中把这座宽阔、坚固的大桥描述成“法国建筑最完美的纪念碑之一”。1870年秋天,法院是莱昂?甘必大政府的所在地,当时这位独裁者被迫乘气球撤出巴黎,而国民议会尚未在波尔多组成。那个恐怖的冬天,德军占领了图尔;德军占领的地区的数量之多令人吃惊。如果说一个人无论来到法国的哪个地方,都会遇见两个最大的历史事件,一个是大革命,一个是德国的入侵,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大革命的痕迹还遗留在成百上千的伤痕中,而1870年战争的可见迹象却已经消失。国家如此富有,如此生机勃勃,她已经能够掩饰起自己的创伤,昂起头颅,再次露出微笑,黑暗的阴影已经不再能够把她笼罩。但是你看不见的东西你还可以听见:你会战栗地回忆起,仅仅在短短数年之前,这个地道的法国省,还处在外敌的铁蹄之下。仅仅是地道的法国式显然并不能构成保护的屏障;对于屡屡得胜的入侵者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挑战而已。然而,和平与富足在事变之后重新恢复起来。在都兰的花园和葡萄园中,那似乎仅仅是一个传说,一个传说国度中的传说。
然而,我提到法院和国王街并不是为了这个曲折离奇的故事的缘故。在我的心目中,有关图尔的这条街的最有趣的事实是,当你沿街道的右侧走向大桥时,你可以看见街对面的房子,巴尔扎克就在那里第一次看见人世的阳光。这个脾气暴躁、令人费解的天才是性情幽默、有趣味的都兰省的儿子。尽管这件事有点反常,但如果你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在他的个性与故乡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尽管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总是在艰苦奋斗,辛苦异常,他有时也表示出他受到各种不同的影响。但是他也拥有快活、满足的一面——这方面在他的《滑稽故事集》中表现了出来——这是该地区古老庄园和修道院的充满浪漫情调和享乐主义的编年史。而且,他也是一片蕴藏了大量历史的土地的产物。巴尔扎克由衷地喜爱君主政体,他的整个身心都被过去的意识所充满。国王街39号——它的地下室和这条街上所有的地下室一样被一间作坊占据,不对公众开放;我不知道是否是传统指定了这个房间,让《幽谷百合》的作者在里面睁开眼睛,来到一个他可以看见和想象出如此神奇事物的世界。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我将高兴地穿过它的门槛;不是为了观赏这位伟大作家的遗物,可能房间里还留着一些,也不是为了神秘的德行,也许四壁之间尚有余馨,仅仅是因为,哪怕就是看一看那平凡的四壁,你就可以获得对人类奋斗的力量的强烈印象。巴尔扎克,在他成熟的洞察力中,他所吸取的人类生活要比莎士比亚之后任何企图向我们讲述它的人还要多:而让他的意识启蒙的这个小场景便是他所横越的巨大领域的一端。我承认,发现他降生在一个“连成一排”的房子里,我感到有点吃惊——而且,这所房子在他出生时刚刚建成有二十年。那一切都是矛盾的。如果选择来享有这种荣耀的住宅不是古老的,而且是深色的,它起码也应该是单独的。
在国王街尽头的广场你可以看见卢瓦尔河对岸的景色,巴尔扎克在他的小故事《石榴村》中对此有过迷人的描述。广场有些自命不凡的气派,从旁边耸立的市政大厦和博物馆可以俯瞰着它,这两座建筑直接面对着河流,装饰着拉伯雷和迪卡尔的雕像。前者是几年前立起来的,非常体面;后者的底座上当然只能刻上“我思故我在”的字样。两座雕像标志出灿烂的法兰西思想所抵达的相反两极;如果在图尔有一座巴尔扎克的塑像的话,它应该立在两者之间。这绝不是说他在感觉和形而上学之间搞折中,而是说他的一半天才朝着一个方向,而另一半则朝向另外的方向。朝向拉伯雷的一面,整体上是向阳的那面。但是在图尔没有巴尔扎克的塑像;仅仅在阴暗的博物馆的一个房间里,有一个构思巧妙但相当粗糙的半身像。我刚才提到的《石榴村》里的那段描述太长了,无法引用;《幽谷百合》中闪光的结构中所编织的那种对风景画的灿烂描述,我在此也没有为之留下空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