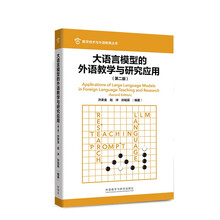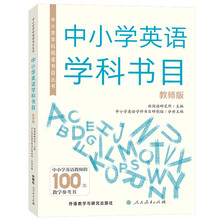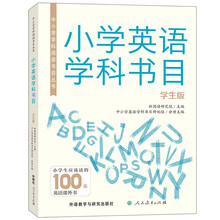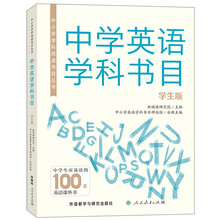随着理论研究意识的觉醒,就会产生研究理论的兴趣,有了兴趣就会去著书立说。远的不说,从黄龙的《翻译学》(1988)问世以来,国内就出版了40多种研究翻译理论的著作(包括翻译史、译论史及有影响的论文集),尽管这些著作在理论研究上水平还不算很高,但总算是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这个进步非同小可,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要知道我国是一个非常轻视理论研究的国家。庞朴(1996)说,中国哲学是明智之学,西方哲学是爱智之学,爱智之学强调追求理论的享受,明智之学强调做人的满足。更具体一点说,我们的传统哲学从本体论、价值观和方法论三个方面都表现出不重视理论思维。本体论强调整体把握,缺乏结构层次分析;价值观强调知情意一体化,从而突出了狭隘的人伦技术化倾向;方法论强调直觉感悟和类比推理,忽视事物之间的层次关系和过度环节,缺乏逻辑论证和逻辑推理。王元化(2001:117)也说:“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体知,重经验而不重理论,对许多事物的道理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弱点根深蒂固,深深埋藏中华文化的底部,或者说融化在中华文化的血液里。我们在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时候,经常有意无意地去掩盖这一严重的弱点。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肩上的一个极其沉重的包袱,或者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进步的一个重大障碍。这个弱点表现在教育上和学术研究上都是用强调务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说法突出实用,反对或歧视理论研究。在翻译界就更突出,公开宣称“翻译无理论”或者“理论无用”的主张,因此理论研究工作很少有人问津。当然现在比较少了。这种局面终于有所打破,怎么能不说这是划时代的进步呢!1.2.2译学建设的指导方针和标准已得到承认。并开始发挥导向作用
译学建设的指导方针首先是董秋斯(195l/1984:543)年提出的:“翻译理论的建设基础有三:正确的科学方法,广泛的调查,深入的研究。”姜椿芳(1986:7-11)在中国译协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在探讨翻译理论方面,我们既要认真汲取国外各个学派的精华,更要创立自己的学说。我国翻译界的先驱和前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们要继承,也要在其基础上前进和发展。过去提过译事三难‘信、达、雅’,但时代的进展要求我们创立适应我国现实、有鲜明特色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