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一梦,然而……
一个文本可以是打开另一个文本的钥匙,就像我们偶尔在别人的书里读到了自己的真理。
如果把法国先锋派文学史家菲利普?雷(Philippe Foret)的小说《然而》看成是挡在我面前的一扇梦之门,开门的钥匙竞已经在无知的我手中攥了多年,那还是我做学生时译的一篇莫里斯.贝莱对梦的解析:
常常梦是对白天忧伤的一份慰藉,或者这忧伤已经很遥远了,在“应该活下去”或“不应该想它”的压力下被渐渐淡忘了。但如果我们再坚持一会儿,任由梦走得更远、更深,在半梦半醒之间,走向别的影像、别的感受,那么就会感觉到一个抵抗的时刻,头脑空空如也,浮起一股焦躁或恼怒。这就像人们靠近那些不该看或不该知道的东西一样,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处于黑暗之中。这就像人们接近那无法触摸到的痛楚,伤口太深,都麻木了;但掀开覆盖的阴翳,走上前去,去触摸、去唤醒那尖锐的痛楚。
——《梦》,莫里斯?贝莱
福雷的梦纠缠着一个遥远的忧伤:1995年的冬天,福雷一家三口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圣诞节,小女儿刚过完三周岁生日,一切美好得像黎明的许诺。而一月初的一个下午,一次例行的儿科健康检查打破了生活的秩序,癌症的阴霾扩散开来,直到死亡的翅翼于1996年4月25日冰冷地
触到了它稚嫩而无辜的猎物。当痛苦隔了时间,忧伤就慢慢学会了隐喻的表达,以谜一样的外表呈现在世界的虚无面前。《然而》的谜面是三位13本艺术家(诗人小林一茶、小说家夏目漱石、摄影师山端庸介)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给读者留下了绳子的一端,你伸手去拉,或由着它自己掉下来,突然砸痛了你,一点眩晕。恍惚间,第四个故事从遗忘中浮现,你发现自己不经意已经跌进那个唯一的、没有尽头的梦中,另一个世界的阳光照在身上,福雷的梦,“每个人的梦”,既是过去,也是整个的人生。 Sarinagara是福雷继《永恒的孩子》、《纸上的精灵》之后在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发表的第三本小说。Sarinagara是日语“然而”的意思,节自小林一茶(1763—1827)一首俳句的最后一词:“我知道这世界,如朝露般短暂,然而然而。”当时年过半百的一茶刚刚痛失爱女,纯美之花还没来得及绽放就凋零了,没有任何理由。面对世界突然呈现的“空”,一茶知道(福雷也知道),什么都不能填满,然而,生活总在继续,虽然从此只剩下了虚空,这虚空已足够填满此后所有的时间和全部的心灵。
我们看到,同样也经历过丧女之恸的福雷试图在他者的文化和风景里迷失,在迷失中寻求一个启示。他的精神苦旅从巴黎到京都、从东京到神户,从小林一茶延伸到另两位日本艺术家的曲折人生:日本现代小说之父夏目漱石(1867—1916)和第一个拍摄长崎原子弹爆炸罹难者的摄影师山端庸介(1917—1966)。“三次都是唯一的故事,当然,也总是同一个故事。……它是每个人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没有什么能强大到足以阻止自身的画面重现,它们从飘浮着幽灵的黄色、抽象的厚重里探出头来。”在他人的苦难中,作者的心灵与虚构非虚构的人物一起在“内疚”和“无辜”的谷底徘徊:自己和他人的疯狂、世界和存在的荒诞、牵不到手的欲爱不能。你知道闹钟最终会响,把你从梦中唤醒,告诉你那只是一个梦;你也知道,在以后的夜里,同一个梦还会继续,然而……
从创作的角度看,《然而》是比《永恒的孩子》和《纸上的精灵》(法文版原名《漫漫长夜》)更成熟的作品,前两本书中绵延不绝的叙事节奏在这里被理智地稳住了,有了停顿和留白。对死亡萦绕不去的回忆,过去残酷的美好和现在不能忍受的缺席,仿佛只有离开,逃到地球的另一端才能找回自我的平衡,找回生活平淡的智慧——禅宗所谓“寂”的境界。在京都的孤独,在东京的迷失,直到在神户的回归,遗忘完成了它的轮舞又回到了记忆的起点,只是这一次,福雷已经学会不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日本也给了作者新的艺术形式和词语的颜色。换一个杯子,生命之酒就品出了陌生的味道。《然而》既是关于日本、关于写作的文学随笔,也是传记、寓言,或简言之小说。俳句是一种起兴,古典的格律或许真的容易平复躁动的灵魂,五七五七七,三十一个音节言说譬如朝露的人生,或者人生的某个瞬间,像一张张掉在地上的照片。一茶、漱石、庸介的故事是三个生命的三十一个断章,三十一种表情,面对浮世的迷惘、诧异、错愕和无奈。
快乐也是有的,只是越美好的东西往往越是短暂,就像所有鲜艳的颜色,总是最先经不起岁月的冲刷,福雷深谙其中的奥妙。他为三个故事选择了不同的颜色,一茶的故事是蓝色的,哀而不伤,不是乐天,不是厌世,是一朵朵“故乡挨着碰着都带刺的花”;漱石的故事是黑色的,理智站在疯狂的边缘,和自己对峙,也和这个世界的变化无常;庸介的故事是灰色的,天地颠倒过来成了黑白照片上不同程度的灰,战争和原子弹是人性的肿瘤,癌的扩散像铺天盖地的灰土,虚无掩盖了毁灭深渊的巨大洞口。而穿插于三个故事之间的福雷自身的叙事是一种黄色的背景,时间剥裂开来记忆泛黄的那点久远的气息,沙子已经漏光,我们依然愣在那里,不是因为在梦里忘了回家的路,而是那扇门后再没有人等候。
很明显,写作是福雷的自我精神分析,“不,我没有走出那个匿子——我一直就不在圈内——我只是围着圈子打转,想象只要有一本都书就可以让我抹却以前的那些书,让产生它们的经验变得生动。这已经是我第二本小说的主题。而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前进过一步。用一种我不怎么明白、更不愿意去承认的方式来看,我只是想用另一本书的形式摆脱自身的故事——之后再用另一本。”这就是福雷的清醒,清醒地看到自己的疯狂,看到疯狂所揭示的智慧。但福雷的情感释放和精神分析并非某种治疗,更不以痊愈为目的。他不愿意伤口结疤,因为结疤意味着忘却,而忘却是可耻的。忘却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种背叛,他要一动不动地注视那份哀伤,直到它静止,静止成“此后”的一种人生态度。
时间过去,《永恒的孩子》成了这份“哀伤的静止”,穿过《漫漫长夜》,《然而》……
在女儿的墓碑上,福雷刻了一行字,詹姆斯?巴里写作的《彼得?潘》开篇的一句:“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除了一个……”
除了那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那个烙在心上、不忍叫出声的名字——波丽娜,漫漫暗夜静静飞翔在纸上的精灵,那个永远的失去和失去的永远。
十年后,福雷依然固守着他心中的哀伤,和妻子阿莉丝一起,和女儿波丽娜一起。今年年初,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书《所有的孩子,除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书名。福雷说:“我确信文学不能拯救。它对经受了一次生死考验的个人来说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方式。写作是为了记忆,而不是忘却。”沉默意味着对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默认,对死亡的一种屈服。写作是福雷抵抗和坚守的姿态,不埋葬过去,和过去一起继续活着,不是不可或缺,只是无可替代。
四
2004年《然而》获法国“十二月”文学大奖的理由是作者“投身于当今真正的文学创作”。的确,在城市的喧嚣和自我的浮躁里阅读这样的文本,容易让人变得婉约,变得古典。虽然有时候痛苦也会尖锐得让人窒息,比如漱石的疯妻和庸介照片上的母亲,被命运湮没,喑哑的挣扎只是一个无谓的动作。幸而我们还有诗歌,还有一茶“然而”的慰藉。仿佛在我之前,我就已经存在了,没有重量的坠落或飞升。最终,我也一定可以学会这种静静的注视,一动不动。无雪的冬天,福雷的文字如一场遥远的雪落在我有些倦怠的眼里,化了,一点指尖抚在琴上的幽凉:
闲庭落松花
自在青苔井底蛙
短歌对夜长
墨深梦浅蝶飞去
青红橙绿舞昏黄
谁在唱?是我,也不是我……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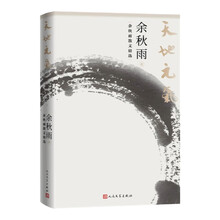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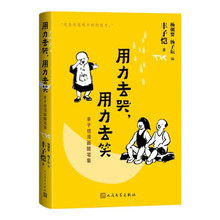



——作家 赵玫
这本书可爱极了,你可以躺着看,你也可以歪着看,你还可以边走边看,——如果你对中法文化的交界处抱有敬意,你不妨正襟危坐。
——作家 毕飞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