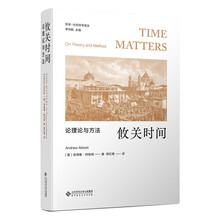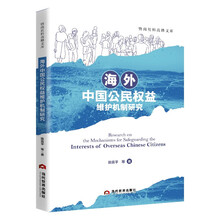第一章 贫困话语的历史谱系
从人类学的视野审视,贫困乃现代文明的建构物,既与资源分配不均有关,也同时源于文化上的偏见,任何一种对贫困的解读和阐释的话语体系都难脱其特定历史和文化的规约。但在当前,不容否认的是源于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贫困话语以普遍主义的强势出现,具有某种话语霸权的特征。在这种话语强势下,大多数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忽视了贫困话语建构的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无心追问它是在怎样的权力庇护下成为球通行的规则、真理的。
本书认为,不可否认现行贫困话语在减贫、缓贫中曾产生过的积极作用,也不能轻率地断定这些话语的对错;问题的关键是要从认识论的角度了解这些观念和知识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以及背后的文化机制,因为任何一种话语背后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预设。需要正视的是,“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视为权力……正是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多重效应。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特定的话语背后总是反映了一定时期群体的共识和一定的权力格局,从而形成了一定的“知识型构”,这种特定时期社会群体以一种总体关系的存在,决定了那一时期解决问题可能的途径和范畴,也决定了那一时期提出问题的方式和思路。因此,深入、系统地考察现行贫困话语的历史谱系对于全面理解贫困,尤其是理解非西方文化语境下的贫困现象就显得十分必要。
贫困谱系学的任务就是以西方历史文化的变迁为主轴,历史地理解贫困,理解贫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从何种角度,以何种权力原则围绕“需要、匮乏、劳动、收入、消费”等概念得到阐释和建构的,主流贫困话语是如何使自己的理论确立权威的,它揭示了哪些真实?又带来什么样的沉默?具体而言,是要弄清楚贫困是如何由神学和道德领域转向世俗领域,贫困如何祛魅(disenchantment)和去道德化从而完成现代性转化的。梳理的目的是“最终要让那些不证自明的东西成为需要研究证明的东西,”以揭示和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自主话语、知识和声音,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以完善人们关于贫困的图像,从而说明现行的贫困观其实是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的产物,总体上是西方经验,尽管它试图成为普泛经验。对贫困话语做如此批判性的历史回顾,明确探讨认知与权力的关系,对思考究竟什么是“贫困”的生活以及体会反贫困首先是反“反贫困话语”的必要性并非没有现实的意义。
第一节 以穷为恶的古典贫困观
作为现代西方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是当今西方社会经济生活诸多观念的主要缘起,对贫困现代性的追寻也必须从这里开始。和许多肇始于古典时代,传用至今的社会理念一样,古典时代的智者对待贫困所持的观念和态度,既有别于中世纪,也不同于现当代;但恰如米歇尔·福柯所指出的,断裂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改变,而是先前认知体系的重新分布,是它元素的重新配置,尽管这里有新的推论性结构规则对知识与真理之性质的重新界定,但是也有重要的连续性。由今人的视野看,古典时代对于穷困的认识是维系在道德之上的,古代智者眼中的“好生活”是为生活本身而存在的生活,而非作为工具为其他目的而存在的生活,因此,贫困不是人们物质财富匮乏的问题,而是欲求的不节制。解决贫困的困扰不是鼓励穷人通过“经济”的方式去创造财富,而是通过训导和教育,用纪律和法令(包括禁奢法)以克服人们的非必需的欲望,从而使人们能够通过自然的符合自身天性的方式满足自己必需的欲望。
一、目的论背景下的古典贫困观
要了解古典时代关于穷人、穷困的知识,首先不得不破除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知识论障碍”(加斯东·巴谢拉语),障碍主要是来自于现代经济学话语所制造的“迷雾”。熊彼特指出,相较于古希腊在天文学、力学、光学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经济学在古希腊人那里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希腊人所谓的经济(Oeconomics)仅指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亚里士多德派所谓的Chrematistics,与经济学这个概念最为接近,主要系指商业活动的金钱方面。而M.I.芬利在《古代经济》中则进一步写道:“马歇尔的书名《经济学原理》无法翻译成为希腊文或拉丁文。一些基本的术语,如劳动、生产、资本、投资、收入、流通、需求、承包商、效用也无法译成这两种文字,最起码在进行经济分析时所需要的那种抽象意义是无法翻译而成的。古代人事实上缺少经济这个概念,更缺少们称之为经济体系的概念成分,当然他们也务农、经商、选购、征税、铸币、存款和贷款,但他们没有把这些特殊的活动在概念编织成一个(帕森斯所谓的)“社会专门子系统。”从人类学的观点看,与现代经济概念相近的Chrematistics在古希腊人的生活中始终居于祭祀、歌舞、辩论、游猎等生活的附属地位,用“经济人”的假设来解释他们的生活近乎荒谬,古希腊人不可能从“经济”的角度来认识贫困。他们真正热衷的是改治,关心的是个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的维护和提升,古希腊哲学家实质上是政治哲学家。
城邦在古希腊人们的政治观念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城邦被视为文明生活存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古希腊智者创建并推衍出目的论以阐释城邦的形成。亚里士多德指出,每一个自然事物生长的目的就在于显明其本性,事物的终点或其极因,必然是达到至善。城邦是出于满足人们的需要自然地演化出来的,其形成是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城邦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种,不能仅限于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而且要超越这样的需要,城邦最终要实现善,这是城邦的自然本性和目的。
由此,古典时代的智者所谓的好的生活的实质蕴涵在具有自身价值的活动当中,从形式上可定义为自给自足的生活,即为生活本身而存在的生活。好的生活并不排斥拥有必须的财产,亚里士多德说,“人若不具备必要的条件,简直就无法生活,更谈不上好的生活。”但获取这样的财产应该不是无限度的,而且取得财产的方式应该是借助于人类天赋的自然的能力,即游牧、农作、劫掠、渔捞和狩猎,这是每个生活在城邦的家庭要掌握的生活技能,依靠这些技能满足家庭的所需,能够最终促进城邦至善目的的实现。而与此同时,另外还有一类赚钱的技术,例如高利贷和以牟利为目的的各类交易,即亚里士多德所称的Chrematistics这样的手段脱离了人类天赋的能力,是不自然的,人们把精力放在赚取更多货币上,而不再是对高尚的好的生活的关注。“生活的欲望既然无穷尽,他们就想象一切满足生活的事物也就无穷尽。”“似乎世界一切事业归根到底无非在于致富,而致富恰恰是人生的终极。”这会让人们忘记了何为“好的生活”,而将居于从属的、手段性的赚钱当成了生活的目的。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贫困就将接踵而至。
二、需求与欲求:产生贫困的分水岭
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写到的尤苏戴莫斯是苏格拉底的论辩对手,他给贫困下的定义是:“凡所有不足以满足其需要的我认为就是穷人,凡所有不仅足够而且有余的人都是富人。”苏格拉底不同意尤苏戴莫斯这个今天看来颇带现代意味的贫困定义。他在答辩中指出,“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所有的虽然很少,却不仅足够而且还有富余,而对于另一些人,所有的虽然很多,却仍不够。”尤苏戴莫斯定义中的需要不但包含生计的需求(needs),也包含着奢侈的欲求(wants);而且尤苏戴莫斯似乎更重视以欲求的不足来衡量贫困,苏格拉底在答辩中很清楚地对两者做了区分,前者以解决生计为限,欲望是节制的,有度的;后者却以奢侈为计,欲望是放任的,无限的。需求和欲求,这两个在西方思想史上界限含糊,相互渗透的概念成为日后西方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衡量贫困的标准和分水岭,围绕欲求、需求和匮乏之间的联系,古典时代、中世纪以及现代社会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解说,但总的趋势是需求逐渐被欲求所代替。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