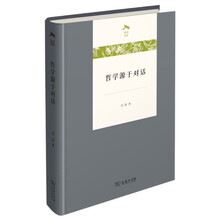在他出生的时候,一个乞丐来到了城堡,他被收留下来而成为这个年轻贵族的教父,这样可以在一生中都提醒他,穷人是他的弟兄。他的护士是农民,而他一生都保留了一点加斯科涅人(Gascon)的口音,法国人说,他的风度也有点像加斯科涅人。他的早期教育是由神职人员完成的,但在20岁时他显示了他头脑的倾向,写了一篇文章来证明异教徒并不值得被永恒地谴责。这篇文章并没能保存下来,但在《波斯人信札》第35篇中可以发现他思想的回音,在那一篇里作为作者代言人(这并非没有争论)的郁斯贝克(Usbek)问“崇高的穆斯林僧侣”杰姆齐(Gemchid)他是否认为基督徒应当永远被谴责,因为他们没有信奉那种他们从未听说过的真正宗教。<br> 他学习了法律。“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说,“他们把法律书籍交到我手中。我试图发现它们的内在精神。”《论法的精神》就是他的研究结果,但并非直接结果。直接结果是,在25岁那年,1714年2月24日,他作为律师(conseiller)进入了波尔多最高法院(Parlement dc Bordeaux)。1716年7月13日,他继承了一位叔叔的职位(prfsident amortier)和财产,条件是采用孟德斯鸠的名字。同时他也结了婚,并在同年生有一子,后来又有两个女儿。作为一位地方官他似乎并非毫无影响。在1722年,他被委托起草一份给国王的关于反对葡萄酒税的谏书,这份谏书在当时获得了成功。作为一个丈夫他并不缺乏礼貌。但无论是地方官还是婚姻似乎都没能充满他的生命。<br> 在他的时代他做爱的次数还算适当,我推断并非只在1715年以前。无论他是否说过女人社会使我们变得“狡猾而不真诚”,他的确说过它会溺坏我们的道德并且塑造我们的品位。我也怀疑当他开始写作时这增加了他用词的辛辣,就像这当然给了他在处理性问题时的自由和兴趣的警觉。他很容易激情澎湃。他说,只要不再相信一个女人爱他,他就会马上和她分手,而在其他地方他用更一般化的术语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悲伤不是一个小时的阅读无法驱散的。有时他的冷漠似乎太明显了,正如一位女士就他在社会上写的书而责备他的那样。也许那是胆怯,他说那是他一生的瘟疫。关于他与女人的关系,无论是家里的还是其他的都说得太多了。至于地方官,他于1726年辞去了他的职务。他发现程序很难掌握,而看到那些他有理由认为没什么天分的人在一些事情上远远胜于他的时候,他感到了厌恶。<br> 他继承叔叔财产的同时参加了波尔多的一个社团,在那里他一度投入于科学研究。他做了一些试验,写了一些科学研究报告,筹划了一部地球物理史,并于1719年发出了调查通知,但好在最后什么也没成功,而这一失败,再加上他外在的缺陷和内在的领悟力,帮助他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他该做的事情上。他患上了“写书症”,并早在1721年就出版了他的《波斯人信札》。将对其自身所处时代的批判放到一个有智慧的外国人口中,以及所有那些东方色彩,如今看来只是平淡得微不足道的东西。但这些只不过是一系列关于从上帝一直到法国上流社会的社会主题和社会利益主题的文章的一个框架或借口——这有点像几乎同时代的《旁观者》(spectator)杂志上的那些文章。<br> 在几乎每封信中都有一些已经被多次引用过的东西,以至于重复它们会让人担心。在一封信里他对很难回答的自杀问题作了几个反思,而在畸形的法律之下那是具有实际目的的。在另一封信里,对于离婚他同样坦率直言,他说得有些道理,希望系上法律已经解开的那个结,而不是将心灵联结起来,这被认为是他们永远分开的原因。先于亚当·斯密,他评论了不同教派的活动,并以非正统的直率指出他们对于改革已确立信仰的滥用所起到的作用。<br> 他以郁斯贝克的身份说:“每一件事我都感兴趣,每一件事都能激发我的好奇。我就像一个孩子,不成熟的器官会敏感地被那些最无关紧要的东西触动。”孟德斯鸠在这些信件中证明了这一点。在进行这些如前所述的严肃讨论的同时,他也描绘了一些仍然生动的人物肖像或者说类型。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