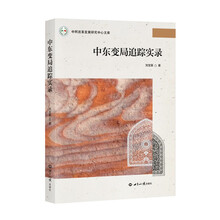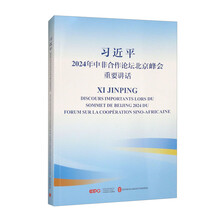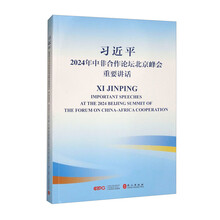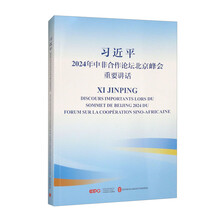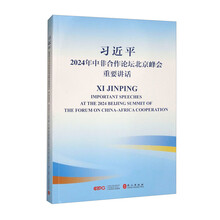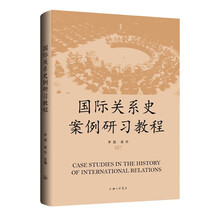国际领域中大多数威胁涉及了诸多复杂因素,这使得它们的直接后果和深远影响都很不确定。当威胁和反威胁措施开始互动时,复杂性又进一步增加了,这一进程最清晰地体现在军备竞赛和贸易战中。即使信息没有受到限制和扭曲,即使主观感知和现实一致,尽管常常并非如此,威胁的复杂性依然是精确预测和评估的巨大障碍。本来客观上很微小的事件,像苏联封锁前往西柏林的通道,在苏美对抗的大格局下也有可能被认为是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举动;而客观上的重大威胁,如全球气候的变化,却可能因为弥散性、不确定性和非常态而被等闲视之。官僚体系的积习、惰性和部门分工也侵蚀着这一进程。大多数国家的官僚机器对军事威胁比对环境威胁更为敏感。<br> 此外,国家安全的负责人对威胁作最坏估计的倾向也加重了这些问题。最坏情况分析的优越性不仅因为它体现着对体系中其他行为者谨慎的不信任——一种有历史根据的立场,也因为它为国内资源分配的斗争找到了一个有利的战斗位置。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