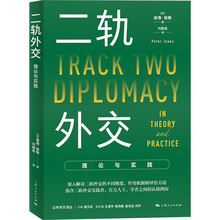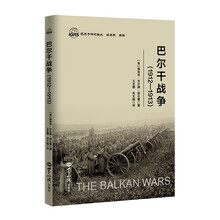这说明传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漏洞。<br> 首先,作为传统军备控制理论基础的威慑思想本身存在诸多矛盾和困境。从逻辑和伦理上讲,以惩罚作为保证手段的威慑陷入了一个道义上的两难境地:有效遏制意味着在遭到对手的第一次打击之后可以发动大规模的报复,使敌人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但这种致无数人于死命的报复性袭击如果发动,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毫无意义,丝毫不能达到减少战争和战争损害的目的。从根本假定来说,军备遏制理论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它的一个重要假定是遏制双方的领导人都是完全理性的,能够在权衡得失算计利弊的前提下作出合乎理性的政策选择,而且他们能够完全掌控自己国家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库。可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一假定很难有足够的说服力,类似希特勒的战争狂人根本不会完全遵照理性的法则行事。从结果来看,遏制战略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一旦遏制发生一次失败,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相关国家的覆灭,甚至会是人类文明的消亡,这和军备控制的初衷背道而驰。此外,军备控制是建立在无法逃避的相互威慑的基础之上的,在冷战时期,威慑关系主要集中在美苏之间,但冷战结束后这种遏制关系变得既复杂又繁多,美苏双边威慑关系逐渐为多边威慑关系所替代,这大大增加了威慑的不可控制性和不可预见因素。<br> 其次,传统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过于依赖主权国家的作用,漠视或忽视非国家行为体可能承担的作用和可能发挥的影响。不可否认,在传统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体系中,主权国家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绝大多数已有的体制是以国家为缔约方签订的条约和协议。但国家主权是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双刃剑,它不时会阻滞和妨碍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发展进程,在某些时候甚至能导致这一进程的倒退。在众多的军备控制体制中,许多国家往往以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为理由,拒绝加入或者虽然加入却作了大量的保留。例如美国以违反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由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PT),导致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军控措施的实施实际上陷于停滞,给世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的进程蒙上了厚厚的一层阴影。有时为了本国私利,有的国家甚至作出导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进程大大倒退的举动。最明显的例子是,2003年美国为了给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扫清道路,拒绝延长1972年签订的美苏反导条约,完全打破了威慑理论的基础。有时某些国家把参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体系与否当作谋求本国利益的政策手段。2003年朝鲜核危机爆发后,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政策筹码。特别是,即便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参与来讲,现存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体系也是不完备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条约、协定、制度或安排是所有主要主权国家都参加或批准的,同时也没有一个主权国家参加或批准了所有的这些条约、协定、制度或安排。<br> 另外,冷战结束以后,冷战时期美苏相对均衡的遏制被打破,美国成为“自罗马时代以来最为强大的帝国”,它“占有世界权势的份额在主权国家出现以来无国能与之匹敌”。国际战略基本结构的变化促使美国开始追求绝对安全,采取单边主义政策,这给国际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进程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变得尤为突出。美国将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相关的国际治理行为当成了追求国家目标的工具。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军控政策标志着美国军控战略的根本性变革,也对国际军控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小布什政府不仅在不同的场合与战略文件中公开表明,传统的军备控制和防扩散指导理念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美国新安全环境,还在具体政策层面以行动来捍卫这种立场,退出被认为是传统国际军控基石之一的《反导条约》以及对印度核政策的转变都是鲜明的例子。以“相互确保摧毁”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冷战式恐怖平衡,以及贯彻这种理念的传统国际军控制度的根基被严重动摇了,国际社会为建立军备控制体系所作的几十年努力,有付诸东流的危险。小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指导下的单边安全战略提高了自身的威慑能力,却对他国的战略安全构成很大压力,从而使其他国家很难在普世的全球或者多边和双边领域达成具有法律意义的军控条约或者协定,从而对自身的军备能力形成实质性的约束。这使得国际军控进程不仅没有出现积极的进展,反而大大退步。<br> 再次,尽管目前已经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的制度性安排和规则,但这些以条约、公约、协定等形式出现的制度大都存在不少的缺点。一是这些制度的规定往往比较模糊,有不少漏洞。例如《化学武器公约》不禁止化学武器的“防御性研究”,这在化学武器的攻、防无法截然分开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为化学武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一个“后门”,也就为彻底消灭化学武器的前景留下了隐患。有很多条约没有规定全面、严格、有效的履约核查措施和监督机制,最明显的例子是《生物武器公约》在最初签订时没有核查措施,而后来附加的核查议定书还没有正式实施。现有的大部分条约和协定没有一个像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那样固定的履约机构,这增加了履约核查的难度,实际上降低了条约的效力。此外,如前所述,几乎所有重要的条约和安排都有一些“关键”国家没有加入其中,使之并不能形成完备的控制体系。如印度、巴基斯坦没有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色列没有参加《化学武器公约》,美国、印度、巴基斯坦没有参加或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最后,有些集团化安排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色彩和政治色彩,影响到其公信力。例如1995年建立的瓦森纳安排(wassenaar Arrange ment),实际上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继承者,它致力于控制武器和两用品向所谓“关切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输出,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br> 最后,虽然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迅速发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进程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却至今没有形成一套为世界上大多数人认同的规范性观念。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