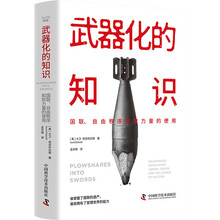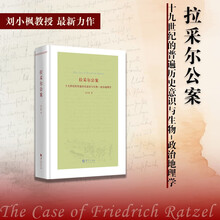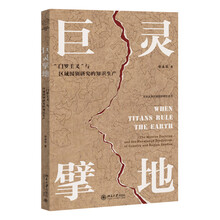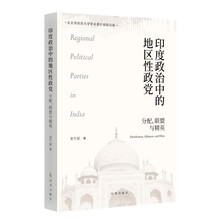聚合与决策程序<br> 尽管在我的模型当中协商是首要的形式,但是协商结论的得出也需要经过一个聚合程序,因为我不仅关注公众意见,也关注公众意志的形成。所有的协商会议都将就二元选择问题(比如,对某提议的赞成/反对)进行表决,每种情况都需要运用绝对多数原则①:协商结束后,就陪审团投的“赞成”、“反对”或“弃权”票,还得进行一次秘密投票。如果三分之二的多数投“赞成票”(就陪审团所投的“赞成”或“反对票”),法案将被通过。如果达到五分之三多数,但不够三分之二多数,那么我将要求陪审团暂不通过议案,让该议案继续保留在公众议程中,以便在进一步的协商会议中做出裁判。<br> 在重议该建议之前,陪审团应该暂停会议,建议发起人可以根据第一陪审团的反馈意见修改他们的建议。因为可以公开获得陪审团的协商信息,建议发起人可以修改他们的建议以满足随机选举出来的陪审团的需求,哪怕另一个陪审团将对该建议进行更深入的考虑。(协商)委员会应确保建议的修改合理,并且反映了协商者普遍的修改意见。任何时候,任何议案的三次无效宣判都将意味着该法案不能通过。当然,如果没有达到五分之三绝对多数,也没有达到简单多数,那么该法案将正式被否决并将退出协商议程,而在传统的程序中,简单多数就意味着建议法案的实施。<br> 如果被否决的议案一开始是通过创制运动提出的,那么在三年内,这一议案将不能通过该机制再次向公众部门提出。当然,在这三年之中,立法部门或司法部门可以要求公众提出类似的问题。如果立法者在协商大会上提出某个问题,他们在三年内也不能采取实质上与被否决议案相似的措施,不过通过创制运动或司法机构可以在这段时期做到这一点。有关分权与制衡的建议体系以及批准权和否决权的更多详情,请参见本书第四章。<br> 议程设置<br> 因为有建议驳回的问题,所以很显然,让某些协商会议为另一个协商陪审团设定议程并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还是需要利用目前的某些把创制引入公共领域的简单机制。大多数情况下,某项建议的倡导者需要征集与该建议相关的部分人的签名。这些签名有时要受到检查以防腐败的发生,而建议本身则要受到某些措词的基本限制以及合理程序的限制,就像受到事务管辖权限制(Magleby 1995,25)。①同时,立法机关或上诉法院有权决定把某些问题提上议程。在本书第七章,我处理了议程设置和形成这一最棘手和最核心的问题。针对这个难题,我认为有两种应对方法:一个较为具体,另一个较为理论。具体的方法就是,在重构的体制中,参加大选的候选人以他们向公众部门提交的基本问题为基础,展开他们的竞选活动。通过这种方式,公民将找到某种参与复决[与创制相对照]议题设置的途径。当然,我不会要求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包含他们将向陪审团提交表决的建议(因为立法者几乎不为公众议程拟定议题)。但经验证明,各州积极利用复决程序的候选人经常以有利于候选人和公众公共决策的政治纲领进行竞选活动(Magleby,1995,29)。<br> 理论的方法就是“公民社会讨论”的形式——公民在他们所在的公民社团(civil associations)中,即在更小的公共领域内形成一系列议题,以便在更大的政治公共领域中得到利用。竞选基金拨款方式的一个根本变化将有利于上述过程,这一拨款方式采用菲什金(1991,99-100)的票券体系框架(sketch of voucher system),同时建立在布鲁斯?阿克曼(1993,71-80)“爱国者建议”(Patriot Pro-posal)的基础上,在“爱国者建议”中每个公民可以向他/她选择的利益集团分配某些公共基金。在第七章,我试图利用这些改革措施提出我自己主张建立的机制。与此同时,假设或当公民社会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的时候,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代表(民选官员或随机挑选进入公众部门的人)能够尽可能地提出各种替代方案和主张,迫使他们利用非党派的力量(与前述CCCA类似的实体)就党派性的争论作出公断。反乌托邦制度的主张者总是用目前存在的问题来衡量进步。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