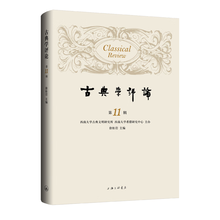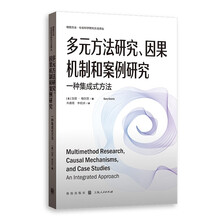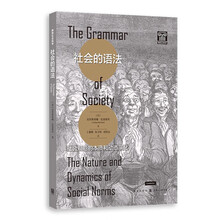第一章 导论
“毒品问题”并非今日社会的新问题。科学家认为,人类可能在5000年前就开始从植物中提取致幻类毒品。①今天,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安第斯山原住民仍像他们的先人一样使用古柯:口里几乎总是不停地嚼着古柯叶或含着一个古柯叶球。鸦片,开始是被当做一种几乎无病不治的万灵药使用的。1805年,德国人塞特纳分解出了鸦片首要的活性成分并将其命名为吗啡,这种活性物质具有10倍于鸦片的效力;19世纪末,科学家在吗啡分子上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化学转变,于是,效能大约是吗啡3倍的海洛因诞生了,它被当做可卡因的非上瘾性替代品投放市场。③
无论是鸦片、吗啡或海洛因,人类探究和应用此类物质的初衷主要是基于医疗的需要。然而,如同20世纪知识领域的两项最伟大突破“核裂变”和“DNA”研究,在给人类福音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两种最大的危险,即“核武器扩散”和“克隆人”一样,19世纪对临床医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吗啡与海洛因,也未可预料地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正如哲学家罗素所言:“科学提高了人类控制大自然的能力,因此据认为很可能会增加人类的快乐和富足:这种情形只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但事实上,人类总是被激情和本能所束缚。”激情和本能驱使人类一次次开启“潘多拉魔盒”,从而引发一系列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目睹了毒品问题的全球化,毒品蔓延的范围已扩展到五大洲的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国麻醉品管制署提供的资料显示,20世纪 50年代,全球的吸毒人数约为910万人,但目前该数字已上升为两亿多人,其中17至35周岁的青壮年占78%;20世纪50年代,全球的毒品交易额为年均20多亿美元,但现在已达8000至1万亿美元。为惩治毒品犯罪、阻止毒品蔓延,世界各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布下天罗地网,但毒品的生产、提炼、走私和吸食非但没有禁绝,反而花样翻新,变本加厉,对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空前的威胁。
中国曾是受到毒品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新中国成立前,全国范围内种毒、制毒、贩毒、吸毒现象十分严重,当时有100万公顷的罂粟种植,有30万人以贩毒为业,吸毒总人数大约为2 000万。以当时人口总数5.4亿计,平均每2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瘾君子。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绝烟毒运动,收缴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厉惩办制贩毒品活动,短短3年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创造了举世公认的无毒国奇迹。
然而,30年后,中国的毒品问题又开始面临新的挑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西方社会巨大的毒品消费刺激了世界各国的毒品生产和流通,毒品问题逐渐演变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开放的中国也无法例外。1991年,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是14.8万人,1992年为25万人,1994年为38万人,1995年为52万人,1997年为54万人,到2008年底,已达112.7万人。如果按每一显性吸毒人员背后至少有4名隐性吸毒人员的国际惯例计算,国内的实际吸毒人员已达450万之众。尽管自2006年以来,中国滥用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人数开始趋于稳定,基本保持在70万人左右,但滥用冰毒、摇头丸、氯胺酮等新型毒品的人却呈不断扩大蔓延之势。①
吸毒在英语中叫作“drug abuse”。意为“药品滥用”。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被称为毒品的药品都不能与其他药品相提并论,因为毒品所造成的身体和精神依赖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毒瘾”,对人类的危害有目共睹。对于大多数成瘾者来说,对渴求用药的强烈欲望是很难摆脱的。而毒品犯罪不仅会与黑社会、暴力、凶杀等联系在一起,成为许多刑事犯罪和社会治安问题的重要诱因,还会导致艾滋病等多种传染病的扩散流行,给人类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与中国百年前遭受帝国主义外来鸦片入侵的灾难不同,今日中国的毒品危害主要已经不是强敌压境,公开入侵的结果,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人们自身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文化理念的演变给毒品的渗透提供了潜在的市场。
经历了旧中国一百多年灾难深重的痛苦,又经历了新中国前三十年艰辛摸索的磨难,迅速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以健康强盛、不受欺凌的姿态立足世界民族之林,是中国人民基本的需求和最大的愿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自由时间的逐渐增多,现代人正面临着更重大、更棘手的问题——物质富足之后精神世界的严重贫乏。如今,“郁闷”二字成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口头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非同步发展,不仅让一些人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产生了意义的真空,也加剧了酗酒、吸毒、赌博及其他不健康的甚至可能导致犯罪的生活方式的蔓延。
人类的认识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是人们普遍的渴望。但是,一旦实现了从贫困向富裕的转化,由充裕的闲暇与过度的消费催生的享乐主义价值观,以及由此造成的普遍的社会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类未来健康发展的更严峻挑战。对此,具有洞察力的20世纪的思想家们早已有过许多经典言论。如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2年就在《预言与劝说》一书中预言:“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可望获得解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永恒的问题’。……自人类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呶、永恒的问题——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怎样来利用它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
今天,我们曾经称之为“西方社会病”①的种种现象,已经不再是一种地域性现象,而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人类普遍的共性现象。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从人类发展的固有规律深刻认识这种现象,对前进中的陷阱或误区保持高度警觉和清醒的意识。
历史的进程不是笔直的,文明的步伐常常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矛盾中交替。保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均衡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深刻的政治艺术,也是中国共产党“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基本方针。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不仅仅是创造美好,也包括战胜罪恶。毒品的演变向我们发出的一个警示是:从发展和进步的根本意义上说,应对新型毒品的挑战已经迫在眉睫,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的社会战略问题。因此,弄清毒品演变背后的社会、文化和人性根源,为禁毒决策提供理论层面的科学依据,已经成为今后禁毒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长期以来,人类始终将毒品当做一种外在的敌人,各国政府的现行政策无一例外,主要集中在如何禁绝毒品和遏制毒品来源的视角上。但是,尽管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却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毒品问题的最后法宝。因此,反对毒品的每一次战役胜利之后,都会出现一个新的战场。
这一现象本身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人类对毒品的认识是否还存在着盲区?面对传统毒品向新型毒品的演变,我们是否到了应该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只是从毒品本身去解读它对人类的危害性,更注重从人类自身的弱点去寻找毒品何以能够持久发生魔力的根源,那么,我们是否可能在对毒品的认识和禁毒的决策方面获得某种新的进步呢?
本书所要揭示的就是这样一个从新的视角所思考的问题。
回顾迄今浩如烟海的禁毒史实和种种理论,关于毒品作用的心理机制以及人性本身的弱点如何受制于毒品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其中的多数研究只是以个人为主体或从生物学角度展开的行为分析。问题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常常是超越纯粹生理的界限而带有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尤其是进入信息社会中的个人,历史因素的积淀和社会文化的浓缩已经以全新的方式笼罩或渗透到个人行为中。
在当代社会中,毒品的流行不仅与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群体紧密相关,而且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特别是某种文化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文化和信息的全球高度一体化,导致个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特征越来越浓厚,在某些情况下,个人行为的反映几乎可以看成是社会演变的缩影。因此,尽管法律可以将个人的行为结果规定为个人意志的产物,并由个人自己承担最终的法律责任,但是,从吸毒行为的形成机制和文化根源中可以发现,构成世界难题的毒品滥用现象,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心理机制的。深入分析从海洛因滥用的明显减少到新型毒品滥用的迅速增加的现象背后不断演变的社会文化根源,对于提升禁毒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无疑是有重要价值的。
如果说,对付外来毒品的侵犯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阻击战,可以用比较强硬和痛快的方法去解决,那么对付现代毒品的渗透,便是一场综合领域的持久战。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