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联播<br> 这是北京电视台1978年1月21日的全部节目──18:00少儿节目;18:35电视新闻专辑《抓纲治国初见成效》;18:50故事片《六号门》;20:30《新闻联播》;20:45《国际新闻》。这份节目预告表提前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当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br> 1978年元旦,《新闻联播》开播。开播首张串联单是油印的,留下多处勾勾抹抹的痕迹,原本排在中间位置的新闻“邓副主席等出席国务院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招待会”被一个长长的箭头勾到了第一条的位置。<br> 三十年后的《新闻联播》,仍然是政治、经济风向标,仍然国脸不老,有人把它作为炒股最好的消息源。<br> “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在报纸上发表时不要再用黑体字。”<br> 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休息时,邓小平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如是说。<br> 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随即请示方毅:今后所有文章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时,是否也一律不要再用黑体字?方毅说:此事由新华社报告中宣部再请示邓副主席后执行。次日,新华社总编室就这一问题给中宣部写报告。邓小平批示:“我赞成。”领袖黑体字语录从此在中国书籍报刊上消失。<br> 20多年后,互联网上流传着不同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新编》,有的是调侃,有的是山寨,有的收集了一些当年毛泽东说过但没有进入老语录的话,比如:“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各种版本,各种字体。<br>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br> 这是北岛写于1976年的诗作《回答》中的头两句。1979年,《诗刊》3月号转载了《今天》创刊号上的这首诗,4月号又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br> 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在北京创建了民间刊物《今天》。在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br> 这一年,王家新刚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年初开学,他班上的北京同学纷纷带着《今天》到校。“诗还能这么写?”大家惊呼着,这本刊物迅速风靡校园。<br> 1979年4月8日,《今天》在玉渊潭公园组织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千人参加,场面非常热闹。警察们在一旁观察动静。<br> 1981年,《今天》被查禁,18个月中出了9期。<br> 而此时,一个全民读朦胧诗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朦胧诗选》成为当时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的床头书。<br> 多年后,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岛写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br> “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br> 1980年,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在《十月》发表,卷首语中写道:“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剧本拍成电影,送审时改名《太阳和人》。影片讲述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坎坷命运:凌晨光一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女儿的出国决定还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女儿反问父亲,“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br> 影片被严厉批判,没有公映。<br> 最难的时候,白桦接到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打来的电话:“尽管沸沸扬扬,(胡)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一再重申他的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br> 党鼓舞我们去改革<br> “民间有种说法,头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会不会导致国人的智力水准下降?”<br> 1980年3月,计划生育政策施行前的座谈会上,一位领导发出这样的疑问。<br>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br> 1996年5月9日,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建国后第一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去世。病危时,陆定一断断续续地说:“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然后,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那两句话,成为他最后的遗言。<br> 据陆定一之子陆德回忆,陆定一说过:“我们是一个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br> “汉朝是8000人养1个官员,唐朝是3000人养1个官员,清朝是1000人养1个官员,现在是40个人养1个公务员。食者之众,生者之寡,国家财政自然入不敷出。”<br> 1996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br> 这一年,在广东某县的官员花名册上,73个部委局办机构,508个正副职领导,其中,县委办公室主任1正14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1正13副。小小县城里,形形色色的科级干部有将近1300人。县口岸办公室的编制为9人,正副主任有7人。<br> “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斤肉。”<br> 1996年12月18日,朱镕基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报告,谈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他如是说。<br> 分税制的结果是: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出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在名义上可以得到财政收入的60%以上,甚至可占70%,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朱镕基说,“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赤字还是在中央。”1996年岁末,朱镕基在北京看话剧《商鞅》时,黯然泪下。<br> “没什么大不了的。”<br> 1996年,深圳一家公司为其丰乳类保健品打出的广告语。<br> 当年初,莫言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出版,小说题目成为议论中心。有人说:“《丰乳肥臀》说它干吗?臊着他们才好呢。那标题——和挂着‘少儿不宜’骗你进电影院的招牌没什么区别。”<br> 莫言专门就公众的议论写成长文《〈丰乳肥臀〉解》,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文中称:“为了消除误会,我不得不解释一番……起码或许可以剖明一下我并无借此‘艳名’哗众取宠的意。”<br> “从25万元改判为1万元,给人一种印象,法律如同儿戏。”<br> 1998年7月8日,19岁女大学生钱小涵(化名)在上海“屈臣氏”四川北路店因被疑偷窃遭遇非法搜身,被迫脱裤受辱,愤而向法院提起人身侵权诉讼,要求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0万元。上海虹口区法院认定“屈臣氏”的侵权行为“非常恶劣”,且原告处于敏感年龄段,被告是港资,资本雄厚,具有较大赔偿能力,判决责令其在报纸上公开向钱小涵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5万元,开了国内大额精神赔偿的先例。“屈臣氏”上诉。这一次,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并未认定“屈臣氏”的侵权行为“非常恶劣”,1999年1月6日,二审改判,将“屈臣氏”给付钱小涵的精神赔偿减为1万元。<br> 舆论哗然。在同样的事实面前,两次判决的差别如此之大,令人惊讶。虹口区法院民事庭庭长朱吉仍然“不认为一审判决有错”。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刘心稳说:“25万元精神赔偿可谓大快人心,改判1万元是不合情理的。”“要么一审法院糊涂,要么二审法院糊涂。”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刘俊海说,“从25万元改判为1万元,给人一种印象,法律如同儿戏。”<br> “就是想活,我们才出来呀!”<br> 民工列车<br> 正月初五,来自安徽阜阳的一列火车开进上海。它被报纸叫做“民工列车”,因为车上全是外出打工的农民。车厢里严重超载,挤满了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叫声和男人的骂声,还有令人窒息的汗臭。有些人的钱包被偷走了,有些人在这数九寒天还中了暑。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他们还算幸运——总算钻进了车厢。<br> 报纸上刊登了一幅照片:火车的车厢顶上都坐着人。车站工作人员好言相劝,说那上面危险,列车会把他们都颠下来。上面的人说不要紧,他们已经把自己绑在车厢上了。下面的人大声呵斥:“你们不想活啦。”上面的人都笑了。有人说:“就是想活,我们才出来呀!”<br> “我们留着这个,不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吗?”<br> 2006年1月5日,《南方周末》的报道《富豪征婚记》中,一名参加富豪征婚的女孩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处女身对于自己的重大意义。<br> “挨点饿吧,我害怕一回去她跳下来看不到,不就白等了。”沈阳一女子欲跳楼,上千人围观,一名看热闹的男子,回家拿了饼干和矿泉水后又匆匆赶回守候,他解释说。<br> “你们外国人就想着怎么展示中国落后的一面。”<br> 2005年荷赛(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一等奖得主米歇尔?沃尔夫在北京街头拍摄一张破椅子时,被一群愤怒的市民团团围住,一位老大妈不满地说。<br> “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br> 2000年10月12日,因《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著作,1997年加入法国国籍的高行健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br> 10月13日,中国作家协会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有许多举世瞩目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此并不了解。看来,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br> 10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最近的行动再次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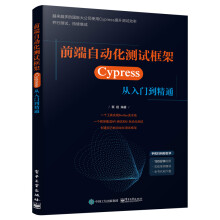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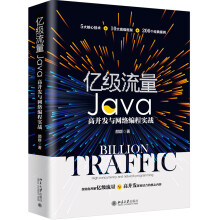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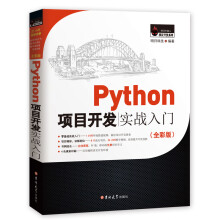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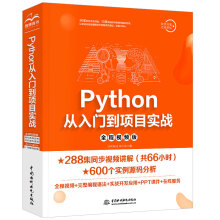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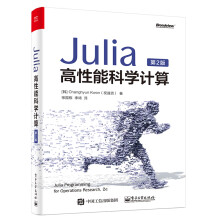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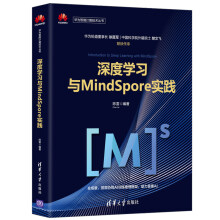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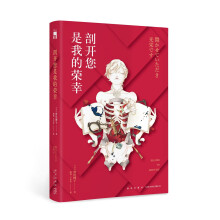
真 话
文/瘦猪
拿到刘青松的这本《真话》那天,我恰好和两个文化界的朋友吃饭。一个某党报的编辑朋友仅看了封底的两段文字便说,弄不好会禁。其中一段写到:“说假话是最大的腐败之一。能够不说假话已经很不容易,更不用说要讲真话了。”我觉得他有些过虑。我问,为啥有些事都出书了,电视台和报纸却不可以呢?他们笑而不答。也许他们觉得问题愚蠢,也许认为我本不该问。如果问世界上最难同时又是最容易的事是什么,讲真话肯定是答案之一。把上面的话延伸一下,讲了真话而无人听见就显得可悲了。《真话》一书的目的就是叫人敢说真话、听见真话、记住真话。
我用了一个晚上看完了书。它以编年体的结构,抉取1978至2008年间真实的中国言辞。这些言辞大体反映了我们30余年走过的路。回顾所来径,不仅有苍苍翠微,更多的是令人百感交集的荆棘和曲折。我们说过,我们不敢说;我们听过,我们装作没听见;我们想听,我们无法听见。但我们毕竟走到今天了。幸与不幸,作为一段历史的经历者,我们有必要记录下来,给自己提个醒,也给后人一份真实的记录。中国文人有这样的传统,留下了各种笔记。当代用语录形式记录历史的书很多,比较受欢迎的有《非常道》、《语词笔记》、《八十年代访谈录》等等,各地报纸也有诸如“声音”等类似的栏目。刘青松以“真话”的角度,切入历史的要害部位,是一个强力补充。三十年的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新和民生,凝练成一句句真人真话,摆脱了史书、档案的暮气,显现出具体而微的气象,它部分可归入正史,部分可归入野史,部分可归入人心所向。
但想倾听全部真话,十倍、甚至百倍于此书的容量而不能。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有雷池和禁地的地方。言论自由的尺度在今天就像一根皮筋,可长可短,它取决于拉皮筋的人,但终于可以伸缩了——你觉得网上可以随便说话,有人也可以随便删除你的话,甚至取消你的说话权利——在过去的某段时期,它是块钢板,成型后,连制造它的人也休想撼动半分。2007年江苏响水县发生一起重大爆炸事件,当地宣传部门竟然说,“在突发事件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同年,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说,“让媒体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是的,若不让媒体和老百姓说话,天才真会塌下来。但实际又如何呢?路漫漫其修远。也写到这,我想起了书中2008年的章节中记录了这样一条房地产的广告:“要提,还要往上提。”——配超短裙美女。
记得小时候有句话,“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刘少奇有这么厉害?还听过一句儿歌“香蕉苹果大鸭梨,好吃不给刘少奇。”刘少奇俨然是个坏蛋了,怎么能向坏蛋学习?后来我长大了,读了一点书,明白了一点事理。它们都是真话,后一句说明明是国家领导,也免不了被打成坏蛋。对比分明的话,最大的好处就是叫人思索那一句是真正的真话。什么是真话?套用官方方式解释,反映客观事实的话就是真话。那么凡是反映客观事实的话,真的都是真话么?刘少奇被打倒被称作坏蛋,客观上存在了被打倒,事实上他就是坏蛋么?有趣的是,本书记录的真话,多在是唱对台戏。例如1983年的章节记载一位妇联干部指责《大众电影》的美女封面说,“难道不能用女英雄代替美女吗?”同年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1983年6月,《人民日报》有篇题为“经济改革的动力是一切向钱看吗?”的社论。针对禹作敏(禹作敏在搜狗拼音里居然不是词组,这也是一种历史吧。)“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宣称。聆听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声音,我感到历史的不可思议,貌似波澜不兴的某些日子,其实在酝酿着沧海桑田般的巨变。那些飘荡在中华大地上的声音,有的和阳光一起洒下,有的伴随着风雨。站在今天回首望去,无论是庙堂的洪钟,还是江湖的弦歌,都显得繁杂四溢,毕竟,不许人说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不能苛求一本书全方位记录历史,哪怕仅仅是说过的话。但有些重大事件的声音还是不该忘记吧。比如1989春夏之交的学潮,真象潮水涌过,不现波澜吗?书中没记录的声音,不等于没发出过,不等于彻底消失。我理解著者的不着半字,正如我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2003年,央视播了一部《走向共和》的电视剧,戏里的慈禧有段台词耐人寻味:“这没影的事儿,他倒好,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了。让洋人骂咱们都是一帮贪赃枉法的人,让海外的革命党有了谋反的口实。听说他自诩敢讲真话,可真话也得看怎么说,有的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讲,有的只能关起门在家里说,内外有别嘛。朝廷养了他这种咬人的狗,可咬谁不咬谁,让他咬几口,要听主人的使唤。不听使唤就乱咬,还狂吠得四邻皆知,没了我的面子,也没了大清的面子。你们说,这种人还留得么?”
你们说,这种人还留得么?这种书,还出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