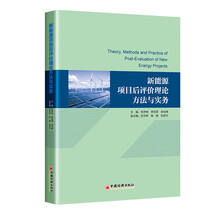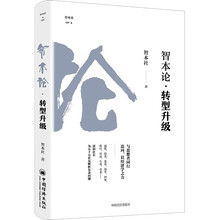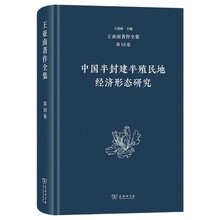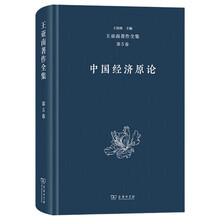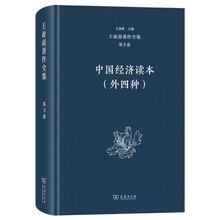第一章 为什么中国经济让人看不懂?
中国奇迹是个谜
西方新词:中国之谜
一直以来,中国这个拥有着广袤土地、博大精深文化的国度,在西方人眼中散发着神秘又迷人的光彩。
1942年,李约瑟时任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当他真正地站在硝烟弥漫的、整个民族为捍卫主权而四处奔命的东方土地上时,发出的疑问却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在欧洲文明史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求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尽管这段话有扬有抑,人们自然地把后一段或许也是发自肺腑的赞叹屏蔽,直奔前面单刀直入的质疑,因为现代科学的缺席正导致那个时代的颠沛流离。而在糟糕的时代提及过往的辉煌,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与不自量力。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的世纪之问,与李约瑟对中国的发问相呼应。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他们的情绪徘徊于失望、沮丧与对未来前景的质疑之间——中国,为何落伍了?中国,还会好起来吗?
今天,距离李约瑟的质疑已过近七十年,他曾经驻足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不过,这里的崛起主要来自经济层面的阐释。持续的冲刺式GDP增长、遍布世界角落的“中国制造”、富有变化的创富者……任何高雅的、庸俗的,以及直白的、含蓄的言辞,只要振奋人心、有关奇迹,都可以一拥而上,以描述这个经历过多年苦难、转型阵痛的国家的蜕变。
当中国的角色发生变化,西方人依然谜团重重。他们已无暇顾及李约瑟当年的困惑,他们更想知道,中国究竟怎样在短短三十余年时间里,创造了西方二百年的经济奇迹?更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中国是在人均资源不足、技术创新匮乏、产权不清晰、计划经济深入社会肌肤、对外不完全开放的黯淡前奏中,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他们在不以为然、质疑甚至嘲笑中,眼睁睁地看着中国这头沉睡的狮子醒来,加速奔跑,甚至一举超过了他们的祖国。
西方经济学理论浩如烟海,却找不到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崛起的理论,任何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套用都显得不伦不类。于是,新的词语出现了——中国之谜。这里所说中国之谜,其实就是中国经济奇迹之谜。
1993年,罗纳德·麦金农提出了“中国之谜”,让他大惑不解的是中国奇特的金融状况:中国财政下降,中国政府打开印钞机,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未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在他看来,“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现象”是“中国之谜”。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的疑问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根据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各国的改革经验,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之后,经济大萧条将尾随而至。中国却出现了改革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的反例。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同样认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原本不可能获得今天如此大的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中国之谜”的瑰丽在于,“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而弗里德曼这位对中国经济“情有独钟”的经济学家甚至把解读中国之谜抬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高度——“只要能够给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可行性方案,他就能够获得,或者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就是中国,短短的时间内以空前的勇气与力量获得繁荣的眷顾,它还有着坚韧的胃口,消化着不少西方国家难以消化的问题,创造了西方世界看不透的崛起之谜。
我们看自己也是谜
西方看我们是谜,我们看自己也是谜。
中国正以令人不可争议的速度崛起,每每想起,“崛起”的欣喜以及油然而生的大国自豪,还是会不经意间流露。诚然,在抽象的GDP增长数字中,我们根本无法清晰地找到我们自己的贡献坐标,那只是一个13亿人笼统的进步符号,不过我们还是情不自禁陶醉在大国繁荣的自豪中。
同时,我们又有新的迷茫。挥洒着大红大紫色调的宏观背景,让你陌生又熟悉。大国正在富有,而有些人仍以“穷人自居”,他们表达自己的情绪,却找不到根源。
在中国,除了崛起是谜,还有很多谜待解。而这些中国之谜,大多是国家崛起与民众崛起之间的流向碰撞。顺着国家崛起的脉络,民众崛起,有些快意顺流,有些则蹒跚逆流。国富背景下出现了一些矛盾与问题。
改革开放把市场引进来,可政治仍在市场的领地内徘徊,牢牢牵动民众喜怒哀乐神经的房地产,价格曾一路扶摇直上,在重拳调控下,才逐渐趋于理性。整个国家财富增长得大快人心,民众的生活已从温饱过渡到小康。
弥漫倾国倾城般华丽与辉煌的时光中,还有很多微妙变局,于宏观至国家微观至个人的举手投足间,隐约浮现,是为前事,亦作今世,更系未来。种种扑朔迷离不断涌现,驱使我们不断追逐真相。追逐真相者鱼龙混杂,扛着时代摄像头的有浪漫救世情怀的夸父,也有只为养家糊口的街头小报“狗仔队”。不管如何,真相正离我们越来越近,不会被历史嚣尘完全吞没。
东西方无人能参透中国之谜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政策可能塑造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上。那些明白怎样读懂这个历史所蕴涵的信息的人们,比从其他任何地方都能更清醒地预感到震撼世界的惊喜。
——约瑟夫·熊彼特
西方学者的委屈
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有着试图控制命运轨迹、扭转宿命轮回的冲动与热情,却身不由己地被命运本身裹挟。
无论是国境之内的“我者”,还是国境之外的“他者”,他们都不断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打量中国,从传统繁荣的世界中心,到萧索凋敝的时代,又到今日之繁华,尝试从密不透风的论证中找到空隙,洞穿歌舞升平背后的隐秘与要害,但也不由自主被真相本身所裹挟。
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漫长性与延续性惊人的国度,拨开弥漫其中的重重迷雾并不容易。
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学者,对西方市场经济制度深信不疑,为其打上“普世”的标签。看似反例的中国崛起,如果被恰到好处地装进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框里,这恐怕是对他们经济理论成果再完美不过的证明。然而,“先有西方经济学的鸡,再有中国经济发展的蛋”的自信预设,反而会成为他们的“有色眼镜”,使其理论视野被蒙蔽。会议桌上、学术期刊中讨论得热火朝天甚至面红耳赤的他们,难以给“中国之谜”一个相对有说服力的答案。
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之所以超越苏联、东欧,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农村,这成为中国劳动力的源泉,在国有部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没有达到整体经济承受能力的底线之前,通过推行渐进式的变革,使大量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
以T?Rawski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劳动力转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事实上,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工业经济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杠杆。
有些经济学家更甚,认为中国经济根本不是一个谜,完全可以用新古典理论进行诠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就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源于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这个谜越来越难解。他们绞尽脑汁,希望把中国这个不再沉睡的巨人装在某个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但是,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由于中国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国情过于神秘与复杂,这些理论往往束手无策,于是有些学者独辟蹊径。
中国特色的制度曾一再被某些西方学者鄙夷,他们打着人道、人权、民主、自由等形形色色的幌子,讥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仍在现代文明尤其现代政治文明的身后跌跌撞撞,步伐凌乱得找不到北。不过,仍有一部分或慈祥温和、或热情奔放、或犀利新锐的学者,对中国的制度赞不绝口,并将其定义为制度优势。
中国的胃口出奇得好,很多国家面临的挑战,都被中国不动声色地消化了。政府“自上而下”发起指令,人民“自下而上”进行参与,中国社会的稳定得到成功维系,并带动了经济层面的改革。约翰?奈斯比特将这种变革称为“中国纵向式民主”,“政府给我们规划了森林,中国的人民将其创造出来。比如说市场经济,政府进行了市场经济的规划,人民群众发挥创造性,建立了市场经济。”
不过,很多人并不认为这些经济学家已经破解了中国之谜。
基辛格,最关注中国国情的国际政治家。这位代表西方首先跟新中国领导层接触的老人,几十年来,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中国每一个细微的变化。他用了一句西方政治家们的口头禅来判断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
而且连研究对象的主角——中国人,也不认为这些“热心”的西方经济学家打造出的中国之钥有多高明。毕竟要打出一把解开中国谜底的钥匙,并非轻而易举,更何况这些异域之眼艰辛跨越文化差异时难免粗暴和擅作主张。更多的时候,他们将精疲力竭打造出的中国之钥示人,并开启洞察大门,却并未给期待者和围观者带来豁然开朗。
东方的视角
各种峰回路转的细节藏匿于中国螺旋式上升的粗线条下,并选择在不同的时机凸现,掺杂着各种理性、非理性的西方学者,会在这些有喜有忧的细节中再次喧嚣,如此反复。当然,中国各路人马也不甘示弱,以旁观者或当局者的身份解读中国谜底。
一头桀骜不驯的卷曲白发、棱角分明、身材瘦高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完全不给西方经济学面子,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的经验证明很多经济学上的东西都是错的,所谓的宏观经济学是彻头彻尾的错,全盘的错。中国在经历了将私有产权铲除得干干净净,又将权力下放,形成地区间的激烈竞争制度,此制度史无前例,是其见过的最好的经济制度。
曾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的老猎户周其仁,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归结为制度成本的降低,“改革引发了中国人学习知识的欲望,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成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2011年,随着两本观点截然相反的图书的出版,中国之谜尤其发展之谜再次掀起争论波澜。
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代表了“中国模式”粉丝的情绪体验与观点表达,该书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既得益于不断开放的市场,又与政府对重要行业的控制密不可分,市场开放与政府推动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而且,“现在中国执政党也是一个完成天命的执政集团。它的天命就是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世界性大国的地位。”
黄亚生的《“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则试图对“中国模式”进行祛魅化,“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中国实行的是价格自由化、企业非公有化,这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模式,中国也在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经济学家张维迎与黄亚生遥相呼应,同样认为不应迷信中国模式。
态度截然相反的模式之争,越来越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分歧。措辞激烈、立场有着非黑即白鲜明性的争辩,散发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无论哪一种主张都难以与现实契合得天衣无缝。有人开玩笑称,张维为教授的书,可以让老百姓多看看以增强民族自信。
黄亚生等人恰是担忧如果过度神化“中国模式”可能导致拒绝深层次改革,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反对“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这一主流观点。不过,即便是那些镀金“普世价值”与“基本原则”的西方经济学原理,也仍在周而复始的否定之否定中摇摆和蜕变,同时我们的文化血缘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将西方经济学全盘照搬视作中国经济变革的金科玉律也需斟酌。
中国经济的“撑高跳”是否完全参照西方的动作要领,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跳得很高(尽管腾空跳起的方式被某些人看来古怪、笨拙),但会存在什么“后遗症”,以及未来到底还能跳多高。
中国既用了“犁”,也用了“剑”
究竟是怎样一种价值观念,或者怎样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和共同的民族起源相互影响着,将中国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史景迁《钱穆与七房桥世界》
“劳动者的犁”与“士兵的剑”
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论述了大国崛起的两种模式:
“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走向同一个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美国人在与自然为他们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在与人进行搏斗。
一个在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另一个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因此,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的,而俄国人的政府则是靠士兵的‘剑’进行的。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而为此目的,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前者以自由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的行动手段。”
中国,既不同于美国的“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也不是“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的复制,而更像介于“劳动者的犁”与“士兵的剑”之间。而且向“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方向靠拢,更具正向意义。因为,美国的持续繁荣,以及苏联在极度辉煌后的瓦解,恰恰证明了美国的崛起模式比苏联的崛起模式更有生命力与合理性。美国的崛起,是民众崛起导致的国家崛起,而苏联的崛起,只是国家的崛起。截然不同的崛起模式,延伸出不同的兴衰成败格局。
人们一边对古老的哲学顿悟——“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深信不疑,一边又不断摸索线性发展模式,以为后来者的繁荣只不过是亦步亦趋地修炼到了先行者的道行。而真正的事实是,经济发展从未游离古老哲学的顿悟之外。
同一经济学原则下,政策可选择的空间很大。经济学原则也很笼统,无怪乎市场、产权、契约、激励等,以保证给民众更多的创富自由。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的观点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提醒:
最为基本的经济原则——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市场竞争、正确的激励、稳健的通货、可持续的债务——并不对应唯一的政策组合。好的制度是那些能够使这些第一级原则充分发挥效能的制度。在好的制度功能及其形式之间,并不存在惟一的对
荣光投下的阴影
荣光背后总会拖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尾巴——“但是”,指望一劳永逸并皆大欢喜的“乌托邦”、“理想国”,不管“土”的还是“洋”的,曾经被煽动者“怂恿”得只有咫尺之遥,然而欢喜触手却只剩夹杂浪漫的流光泡影。
冷幽默“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恰到好处地暗讽桃花源只是迷梦。即便被很多人视作淘金天堂的、连华尔街路旁树叶上都浓妆涂抹着繁华气息的美国,也有难言苦衷,一场金融危机让“经济霸主”颜面尽失。
告别计划经济实行改革的中国,也涌动着不少暗流漩涡。2003年,任仲夷表示,中国改革仍未过大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高效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其背后的阴影已不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腐败、贫富差距……
新的商业秩序兴起,技术革命浪潮席卷社会,形成更为强大的生态系统,今天的我们,见证着崛起的荣光,也经历着伴随而来的担忧与坎坷,他们如同硬币的两面,快速旋转,折射出模棱两可的光线。而要试图看清旋转背后藏着怎样暗合天意的密令指派,就不得不在时间里辛苦耕耘,以求寻得时间洪流中被一一展开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线索。
自主创富是不是最终谜底?
在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中,东方涌现出一块巨大的、美丽得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摆脱一切,独自浮现在天际,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像是来自陌生的远方的一个问候……
——卢森堡《狱中书简》
中国奇迹之谜的最终谜底:自主
国富的外壳再坚硬,里面隐藏的也是一个个脆弱而敏感的人,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希望过上好日子,这才是国富的终极目标,即藏富于民。
有无数个路径通向“藏富于民”,如体制变革、法治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回归、对外开放,它们将“藏富于民”从纸上政策层面深入到现实层面。所有要素,归根到底不外乎自主,它才是中国奇迹之谜的最终谜底。
漫长的时间经络不断分化、拔节和抽芽,有选择、传承与背叛,所有时光之尺的衡量标准,都逃不过“自主”两个字。不管国富民富,不管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的发展,皆基于民众自主创造。
制度上的豁然松绑,带来发展自由。空间骤然解放,人们更轻松施展拳脚,各方沉寂或被羁绊的同时,人们职业流动的自由度也逐渐增加,从板结状态进入开放状态,“分配”这个曾牵动无数家庭饭碗的名词,渐渐蛰伏或消亡下去,跳槽成为家常便饭。之前影响工作横纵向流动的因素如阶级、成分,逐渐退出社会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学历、素质与技能。
期待更多的空间开放
主张自由最大的后果是,各种有形的门槛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名义上的准入券。但这些自由还远远不够。
有些自主创富,尽管已经存在,甚至一度要被潜移默化为共识了。不过,当触及到某些利益或情绪时,还是会出现反复;有些自主创富,还会被权力绑架,如权贵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的自主还只是“画饼充饥”,虽然政策上已经趋于理性,但现实中却牢牢竖着一道玻璃门。
自主创富在中国跋涉中遇到种种问题,政府应将自主袋子的敞口打开得更大一些:需要政府在政策层面的认同与鼓励的,步子迈得大一些,坚定一些;已经在政策层面承认的,加强在现实层面的兑现落实,并坚持下去,避免政策反复。政策上的反复,只会弱化人们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吞噬民众创富的信心与热情;政治改革再难啃,也要矢志不渝地走下去;割断资本与权力的不正当联姻,让权力回归自己的正常角色;建立法治市场经济,依法行事……
一位外国人经历中国之行之后写道:“……回忆起来如在梦境……我已清楚地看到亿万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正在迈步走向更好的生活……在这片混乱中孕育一种坚定的目的感……”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我们信心十足地把未来灌注得汁液饱满、光鲜照人,恰恰因为我们相信,时光这条巨流终会涤荡出自由的透亮本色,一切豁然开朗,如月色倾城。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