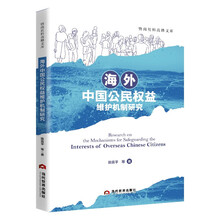第一部分 一种非常普通的文化
第一章 一个共同的场所:日常语言
《没有个性的人》揭示了对独特性或奇异性的侵蚀与嘲讽:“或许正是小资产阶级效法蚂蚁才加速了巨大的并且是共同的新英雄主义曙光的到来。”的确,这个蚂蚁式社会和群众一起偶然形成,而群众首先服从于测量水平的理性划分。社会的浪潮不断壮大。随后,触及到机器拥有者及其管理体系中容纳的干部和技术人员;最后,还蔓延到自认为受其保护的自由职业以及美妙的文学家或艺术家。这股浪潮卷起并冲散了那些曾经如岛群一般的作品,如今它们变成了大海中的水滴,变成了语言传播中的隐喻。语言的传播不再拥有确切的作者,而变成了他者不确定的话语或引用。
“每个人”(Chacun)和“没有人”(Personne)
诚然,在过去,有一些事情是由“共同的”疯狂与死亡中的一致性所组织的,而非技术合理性水平的提高。于是,在现代性之初,即16世纪,普通人(Ihomme ordinaire)都带有一些普遍的不幸,而且他们将这不幸变得微不足道。正如讽刺文学,特别是北部国家和已经受到民主主义影响的国家特有的讽刺文学所表现的那样,与诺亚方舟相反的是,普通人“登上了”狭窄的满载着疯子与必死之人的人类之舟,因为它将驶向歧途与堕落。于是,在这里,他们被套人了共同的命运(Ie sortcornmun)之中。因此,这个被称为每个人(Chacun)(这个词泄露了名字的缺失)的反英雄同样也是没有人(Personne,Nemo),恰如英语中的Everyman(每个人)变成了Nobody(没有人),或德语中的Jedermann(每个人)变成了Niemand(没有人)。这位反英雄总是他者,没有自己的责任(“这不是我的错,是另外一回事:命运”),没有界定个人领域的特殊属性(死亡将所有的差异一并抹去)。然而,在这人道主义的舞台上,他依然在笑着。在这一方面,他理智而疯狂,清醒而可笑,这命运,所有人都无法摆脱,它将每个人都追求的豁免化为乌有。
其实,有一种文学通过其创造的爱笑的匿名者道出了自己的地位:因为文学仅仅是一种虚构,所以它是对注定要毁灭的幻景所构成的世界的真实表现。“无论谁”(n’importe qui)或者说“所有人”(tout lemonde)都是一个共同的场所、一个哲学地点(topos),这个普通的人物(所有人和没有人)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即讲述虚幻且疯狂的文字作品与死亡、即他者的法则之间的普遍关系。他在舞台上将文学的定义当作世界,将世界的定义当作文学来演绎。普通人自己在其中并没有得到展现,而是在文本中并通过文本来展现,另外,他还传播了特殊场所的普遍特征,而闪耀着学者智慧的疯狂言论就扎根在这一特殊场所中。他既是人道主义讽刺的噩梦或哲学梦想,又是参照系的外表(共同的历史),此外表使写作——这写作使其可笑的不幸得以面向“所有人”讲述——变得可信。但是当精英主义的写作将“庸俗的”谈话者当作有关自己的元语言之装饰来使用的时候,它同样任由那些将写作从特权中赶走并将其从自身之外吸纳进来的东西暴露出来:一位他者,既非上帝,亦非缪斯,而是匿名者。写作脱离了其专属地点之后误人的歧途便由这个普通人勾勒出来了:萦绕在写作周围的怀疑的隐喻与偏离,“虚荣心”的幽灵,他与所有人的关系与豁免权的丧失之间的关联,以及与自己的死亡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一切均赋予写作谜一样的形象。
弗洛伊德与普通人
关于这位“哲学”人物,当代人的评价提供了一些或许更加意味深长的例子。弗洛伊德将自己的分析致力于文明(《文明的苦恼》。)或宗教(《一个幻觉的未来》”)——文化的两种形式,当他将der gemeineMann(普通人)作为这些分析的开端与主题时,忠实于阐明(Aufklgirung)的弗洛伊德并不满足于将精神分析的成果(“一种研究方法、一个公正的仪器,可以说就像微积分学一样”)和“大多数人”的蒙昧主义对立起来,也不满足于将大众的信仰作为一门新的知识联系起来。他重新拾起的不仅仅是从前的图式,从前的图式不可避免地将精神的“幻觉”与社会的不幸同“普通人”(Ihomme COIIXFflU,11)联系起来(这是《文明的苦恼》中的主题,但是弗洛伊德认为,与传统相反的是普通人不再笑了)。他希望将自己具有开拓性的“阐明”(elucidation)(Aufklgirung)与这个“幼稚的”多数派联系起来。将“为数甚微”的可以将工作升华为乐趣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丢在一边,于是离开了这些“少有的当选者”——不过,他们指出了弗洛伊德的文本形成于其中的场所,弗洛伊德与“普通人”达成了协议并使自己的话语与大众相吻合,而大众共同的命运乃是被繁重的劳动诱骗、挫败和束缚而屈服于欺骗的法则和死亡的劳动。这份合同类似于米什莱的故事中与从不言语的“人民”(1e Peuple)签订的合同,它似乎必须允许理论扩展至普遍概念的范畴并以历史的真实为依据。它为理论赢得了一个确定的场所。
诚然,多亏了宗教中的上帝,普通人被指责造成幻觉,即“揭示这个世界所有的谜语”并“确信有一个上帝在关注着他们的生命”这一幻觉。从这个侧面来看,普通人(通过对未来的保障)轻松地赋予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对自身地位的保障。但弗洛伊德的理论难道就没有从其援引的普遍经历中得到一点类似的益处吗?作为抽象的普遍形象,普通人在其中还扮演着神灵的角色,即使堕落并与迷信的大众融为一体,他的作用总是可以辨认出来的:他为话语提供了方法,以推广特殊的知识并通过全部的历史来确保其有效性。普通人准许话语超越其限制——仅限于某些疗法的精神分析能力方面的限制,同样也是整个语言活动自身的限制,而语言活动缺失了被普通人视作参照系的真实。他既肯定话语的不同之处(“清晰的”话语依然有别于“共同的”话语),又肯定其普遍性(清晰的话语讲述并解释共同的经历)。无论弗洛伊德对“社会渣滓”(Ia racaille)持有怎样的个人意见并且在米什莱关于人民的乐观主义观点中,我们都能找到其反面,普通人总是以话语作为综合与委派的原则:他准许话语如此表述:“对所有人而言,这都是真的”,“这是历史的真相”。普通人在这里以上帝昔日的方式发挥着作用。
不过,年迈的弗洛伊德恰恰预料到了这一点。他讽刺自己的作品,说它“完全多余”,纯属无聊之作(“我们总不能一天到晚吸烟和打牌”),只是“高雅话题”的“消遣”而已,但正是这些话题使他“重新发现了最平庸的真实”。他将该作品与自己“之前的研究”区分开来,之前的研究与某种方法的规则相关并建立在特殊情况的基础之上。但此处不再涉及小汉斯、朵拉或施雷勃。普通人首先反映了弗洛伊德的道德愿望、伦理学普遍观点在其职业领域中的回归,相对于精神分析方法而言的增加或偏离。由此,他阐述了知识的倒错。其实,弗洛伊德嘲笑这个未来的“文明社会病理学”的引言,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其谈论的并与之对话的普通人,在他的手中掌握着某些“平庸”苦涩的“真相”。他的思考最终发生了转变。“面对毫不留情的指责,我绝对接受”,他说,“因为我没有做好”。在那里,他被看作与所有的人一样,而且,他笑了。一个具、有讽刺性但充满智慧的疯狂与这样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即丢失了某种能力的独特性以及所有人或没有人重新置身于共同的历史之中的事实。在《文明的苦恼》这个哲学故事中,普通人就是交谈者。在对话中,他是智者与大众的接合点——他者(所有人和没有人)回归到与此区分明确的位置上。他不止一次运用平庸勾勒出特殊性的流露以及智慧向着普遍前提的传导:对于那些严肃的东西,我一无所知。我无异于众人。
“丧失”、“抑制”、“爱神”、“死神”等,在《文明的苦恼》一书中,这些技术研究的工具开辟了从傲慢的阐明(Aufkliirung)到公共场所的途径,而弗洛伊德的文化分析最显著的特征首先就是这一逆转的轨迹。一个看似细微但却至关重要的差异将其结果与文化专家所分配的陈词滥调区分开来:这些陈词滥调指示的不再是话语的对象,而是其位置。平庸的不再是他者(他者负责使人们相信其导演者的豁免);而是文本的创作经历。当普通人变成叙述者的时候,当他确定了话语的(共同)场所以及话语展开的(匿名)空间的时候,文化的临近便开始了。
相对于任何其他人而言,这个位置对谈话者来说都并非更加确定。它是一个轨迹的终点。不是某种状态、缺陷或最初的恩赐,而是一个转变的结果,是偏离过程相对于被调整并可以弄虚作假的实践而言的效果,是普通事物在某一特殊地位之上的洋溢。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是这种情况,他在结束最后几篇关于普通人的故事(就像人们结束一个死囚那样)时用了“研究”(travaux)这样的术语:通过对知识的虚构来实现哀悼。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