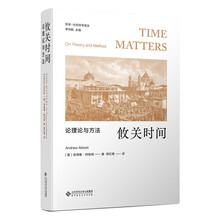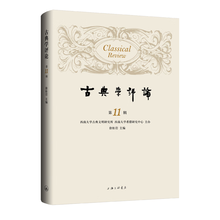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星丛中,有一颗星闪烁得很快乐,很诡异,也很严肃。他快乐,因为他在不断地揶揄着当代布尔乔亚世界中人们追逐那个永远不可企及的剩余快感的执着,嘲笑着那个崇高对象的飘渺性。他是个患有“症候瘾”的导游,在我们熟视无睹的经验生活和文化“景点”中,他不断地捡拾那些“空白”:在我们打开可口可乐瓶盖的刹那间,他帮我们发现从里面“蒸发”出来的那个“对象a”;在资本主义用牙膏上“30%免费赠送”的广告忽悠大众时,他也以“想割下白送的30%放入自己的口袋”的机灵鬼方式,替大众反忽悠了资本主义一把。他诡异,因为他在希区柯克、大卫·林奇、塔可夫斯基等大师导演的电影和一段段难登大雅之堂的笑话中,例证着他对艰涩的晚期拉康哲学的消化和转译,敷陈着他对“实在界”、“创伤性内核”、“凝视”等等概念逻辑的新颖论证。他又非常严肃,他在电梯里发现了关门按钮给人的只是认为自己行为富有成效的“误认”,然而他却在这里偷窥到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真理:公民的政治参与只是在政党政治的饕餮大餐之后捡拾些残羹冷炙充饥,指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整体的易碎性。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