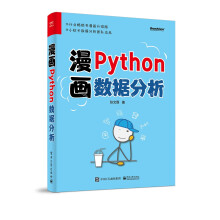特稿<br> 往事半苍茫(上)——成舍我的办报生涯<br> 民国初期的报人,因时代不宁,经历曲折甚而奇崛者为数不少,他们的办报生活,有的自立门户,独往独来,以一支孤笔向强权社会挑战,如林白水之于《社会日报》、邵飘萍之于《京报》;有的办同人报,说自己话,在政治夹缝中左冲右突,成就其事业,如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三驾马车”创办的《大公报》;更有无计其数的人,在依附报馆为稻粱谋的同时,自我奋斗,独树一帜,成为报人中的佼佼者。如果要找出一个人,都经历过这几种报人生活形态,且在每个领域都留下传奇故事的,则非成舍我莫属。<br> 翻开成氏年谱,他的报人生活,从开始记者生涯的安庆《民暑报》、沈阳《健报》、上海《民国日报》、北京《益世报》,到独自创办的《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南京《民生报》,再到与同人发起的上海《立报》、香港《立报》、《自由人报》,其丰富多彩,流光溢影,本身就是一部报业的风云史。<br> 在以上一系列报纸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显现着中国报业发展嬗变的轨迹。成舍我的办报经历,从辛亥革命发生直到国民党统治结束,跨越了整个民国时期,既是一个情节曲折、高潮迭起的精彩故事,也是那一时代报人生活的缩影。要说新闻是历史的独特见证,要说优秀的报人是社会政治生活的记录者和参与者,成舍我讲述自己的办报生涯,算是一个难得的典型例证。<br> 因父亲蒙冤对报纸发生兴趣<br> 成舍我原籍湖南湘乡,1898年生于南京下关,“舍我”原是他的笔名,取自《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也透露他青年时代自视甚高,有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一面。“舍我”既随文章传噪一时,本名“成平”也就鲜为人知了。成舍我的祖辈从湘军到江南镇压太平天国,以后定居南京,这一段家史,见于他在《世界日报》上的追记:“自太平天国之役,曾国藩以湘军转战东南,湘子弟弃耕来从者数十万众,而吾邑豪杰之士,起自田间,立大功官至封圻者,乃多至不可胜数。先大父春池公,亦以此弃故业,佐国藩弟国荃幕,历官江浙,此为吾家百余年来有仕宦之始。”但是,到他父亲成心白这一辈,家业已荒芜,沦为既无田地也无房产的平民,靠着一份收入微薄的差事,为人司笔札养家糊口。大约在1900年,成心白因参加平定地方土匪有功,由乡人保举,获得一个九品候补官位,分发到安徽候缺。直到1906年,才被派为舒城县监狱典史(典狱长),然而不过两年,监狱发生暴动,数十名囚犯破狱出逃,成心白奋力追赶,在与逃犯搏斗中被殴成重伤。这个事件,经各报的传播,当时成了一条大新闻,连上海《申报》都发表了详细的报道。<br> 按清廷成规,看守人员疏于防范而造成囚犯穴墙而逃,称作“越狱”,要问罪于典史;而囚犯结伙破狱出逃,称作“反狱”,属于狱政管理问题,知县要负责任。在往上行文呈报时,为了将“反狱”改称“越狱”,求得减轻刑责,这位陆姓知县向成心白提出,愿以纹银二干两,换得他同意共同遮掩此事。尽管这是一笔大数目,梗直倔强的成心白却不愿代上级受过,于是陆知县一边在报告中把逃案归罪于典史不尽职,一边联络上海各报驻省城安庆的访员,徇私发布对成心白不利的新闻,成心白则有口难辩,始知舆论之利害。一个小小的知县,为了保住官位,不惜重金贿赂,使出浑身解数,为了什么?成舍我当时不到十岁,对此事却印象颇深。<br> 那时候做知县的,都有的是钱,最大的财源,就是收田赋,大的县份,一年究竟收多少,都没有数儿,也没法统计,大概都是收十块,往上报一块,其余九块,都可入县太爷的“腰包”。我记得当逃狱事件发生时,大约是在阴历七、八月的时候,正是田赋开始征收时期,所以他宁可给我父亲两千两银子,替他顶罪,也不肯丢官,但我父亲的个性也很倔强,宁可不要他的银子,也不肯替他顶罪。因此使知县恼羞成怒,他的呈文硬说是先有囚犯挖洞跑了几个人,后来才打架的。因在未定案之前,上海各报已有了消息,后来知县被撤职,我父亲也被撤职。<br> 成心白因此丢官,心有不甘,带着一家人赶到安庆,住在湖南人聚居的大杂院“曾公祠”里,希望向上级机关面报实情。就在这当儿,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神州日报》派驻安庆的访员方石荪。方石荪也是湘人,十分同情成心白的遭遇,乃撰一长文,详细叙述舒城监狱暴动真相,很快刊登在报上。因为这篇文章,成心白终得“平反”,典史却是做不成了,为前途计,考入安徽省安庆高等巡警学堂深造,两年后毕业,又被派到凤台县任警察局长。<br> 因父亲受诬陷一事,新闻记者这个职业给少年成舍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是报纸的访员,一个收受了钱财,可以避重就轻把囚犯“反狱”说成“越狱”,使他父亲蒙冤丢官;一个忠于职责,在报上仗义执言,使得案件真相大白,而舞弊的知县也被治以应得之罪。这种景况,让他深切感受到了新闻纸的强大力量,从个人福祸到社会生活,无不有所作用。成舍我到晚年对此事念念不忘,足见这段经历对他后来选择报人生涯,有着直接的影响。<br> 成舍我的求学历程十分艰辛,他父亲位卑禄薄,任典史时,每月俸银仅二两九钱,家里人口又多,子女四人,绕膝索食,因此无钱供给上学,他跟着父亲读书写字,直到十二岁才进小学。清宣统元年(1909年),成舍我入安庆湖南旅皖第四公学,“不一年,自初小高小,拔升至中学。顾家愈贫,境愈困。书值百钱者亦不能致,须昏夜借写。不能具校服,有操演或集会,均摈不得与。又积欠学金过巨,则不与试。卒至辍学”。成舍我十四岁那年,武昌起义的消息沿着长江传布开来,不久,革命军的势力蔓及安徽,并很快攻克他父亲任职的凤台,旧的制度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成心白自也不能幸免,结果是保了命、丢了官,带着一家人逃走。成舍我到晚年时回忆起来,依然是历历在目:<br> 当时革命军占领的地方,很多县长都被杀了,我父亲是警察局长,居然被放走了。因为他的为人不错,在地方上做的很好,也没与人结怨,否则也会被杀的;……我父亲决定先回安庆,那时候地方治安很差,听说到处都有土匪,如果人少,携带的行李财物,一路上一定被劫光。因此,我们是联合很多人,集结几十条船一块儿走的,比较安全。<br> 因皖北淮河流域,在清末时本来就不太平,革命军把清军打垮之后,很多清兵都做了土匪,他们都有枪,到处杀人掠货。我们一路上果然多次遇到土匪劫船。船行在河中心,两岸都有土匪,对着我们的船开枪,叫停。船上也有很多人有枪,就对着岸上开火,就这样停停打打,打打停停,逃到一个津浦路的车站,大概是在蚌埠。记得当时还有火车,我们就乘火车到了南京。当时正是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时候,我们就住在下关,眼见炮火连天,大人小孩,莫不触目惊心。我们稍作停留,就搭民船逃到安庆,那时安庆也已经被革命军光复了。这回我们全家,才总算是安全到达目的地了。<br> 回想这一路的情境,真如做了一场噩梦,梦见死里逃生了。<br> 一家人回到省城时,安庆已经光复,新政府也已成立,到处洋溢着一派新气象,成舍我的父亲因是旧官,在新政府中又没有关系,就只好居家赋闲了。但成舍我却闲不住,街头张贴着革命党招兵的告帖,号召爱国青年都去投革命军,推翻清王朝,告帖上充满鼓动性的语言吸引着他,跑到青年军的招兵处,抢先报名投考。对自己的这段“革命”经历,成舍我一生都引以为荣:<br> 那时候我才十四岁,是个小孩子,大概是心理上所感受的,觉得当时社会上的坏人坏事太多了,觉得只要参加革命,就能铲除“坏人”、“坏事”,所以我就去投考了。记得他们是招考三个队,每队五百人,总共一千五百人,我是考取了第一队。在考取时,军监韩衍对我们几位成绩最好的入说:“你们的成绩很好,我各送你们一本书吧。”于是他就拿来几本《华盛顿传》给我们。他说:“你们很不错,希望你们做未来的华盛顿。”因为那时候提倡革命时,都提倡崇拜美国华盛顿。<br> 我入伍时个子很小,发给我一支枪,和我的人一般高,现在回想,那时青年军也是胡闹,他叫我们去找汉奸,因革命党刚把满清打倒,但许多人想做汉奸,再把满清恢复起来,所以要抓他们。我们要轮班巡夜,查旅馆,有时从晚上搞到天亮。还有几次指说某人是汉奸,去把他们打掉;我还算好,没有派到过这种任务。后来,连都督都管不了他们了。<br> 成舍我开始给报馆投稿,大约就在这时候。据他自述,引导他走上新闻之路的启蒙老师,就是几年前为他父亲在报纸上申冤的《神州日报》访员方石荪的儿子,名叫方竟舟。方竟舟时年二十出头,素有继承父业、从事新闻工作的愿望,得知成舍我小小年纪,就有当新闻记者的大志,乃引为同道,时加鼓励,向他讲解报纸对于影响国家人心、转移社会风气等方面的作用,指导他就身边见闻,撰写新闻稿件、小说、杂文等,每写一稿,必帮助修改润色,并代向报馆投稿,常被采用。<br> 这时候的成舍我一心向往革命,为建立共和国出力,一年多的时间里,都和同伴们一起在省城内打打杀杀,把安庆闹了个天翻地覆,不可收拾。不久,当青年军被改编为正规部队,准备向南京开拔时,若不是他父亲上船阻拦,成舍我或许会成为一个职业军人,而不是新闻记者了。对当时的情景,他有以下回忆:<br> 那时候的都督是白(柏)烈武,白烈武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一直到袁世凯做总统,白烈武仍做都督。他来之后,就先叫青年军改编,而韩衍不答应,不久,韩就被人暗杀了。据说就是白烈武派人杀的,因为这一千多人都有武器,后来青年军就被解散了。那时,革命军已把南京光复了,黄兴做留守府的留守,他组织了一个入伍生队,白烈武就获得黄的同意,把一部分青年军送到南京入伍生队里去,我就自愿参加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