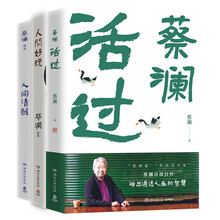这种由资产阶级而闻到革命的气息,而真去革命,而把革命象征了,不是一个很合理的进展么?合理是真的;但也许太合理了,我在《在黑暗中》看到的丁玲是这样;在《韦护》里看到的仍然是这样,在《一九三。年春上海》看到的仍然是这样——倘若就这样下去,我想不会有一天不这样的,也许因为时间的关系,在(《在黑暗中》里不得不穿旗袍或马夹;在《一九三○年春上海》只好穿蓝布裤褂之流的东西,我不愿意替别人检定意识,说不愿意是瞎话,实在是不会,但是丁玲的意识却很明显:她彻头彻尾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典型女性。
在这里,很奇怪的,我想到扑火的蛾子,无论原来是在树丛里,墙角里,只要见到一丝光明,也要去扑,被纱窗隔住了,还要停留在那里,徘徊着往里窥探,希望可以发见一个空隙,钻了进去。但这个联想实在不恰当,我承认我们的革命家闻到了革命气息,有的也真的去革命了,但是大部分闻到这气息的时候却往往在跳舞厅里,喝过了香槟酒“醉眼朦胧”的那一霎那间。我的良心不使我把丁玲归在这一类,但是除了这一类外,我却也再找不到更适合的一类了。
但是,实在说起来,还不这样简单,在她这一些作品里,我看出了她的一个特点——黏质的惰性。这种惰性我自己也感到过,尤其是在读书的时候,只要一想到发奋读点书,总想明天开始罢,然而明天成了今天,还明天开始罢。就这样明天下去,终于也不开始了,在某一种时候,丁玲也实在被革命气息陶醉过,但是她仍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向前动一动。自己做些美丽的富有诗意的梦,她微笑着满足了,也许她也有“来了”之感罢。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