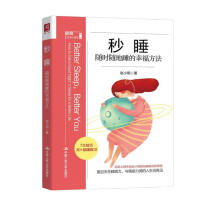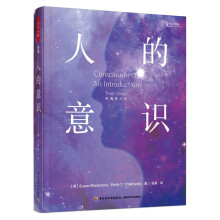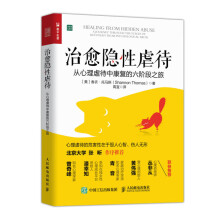第一章 诗的机器
大多数人至死不曾发挥自己的能力。他们生时带来万贯财富,却一贫如洗过完一生。
——奥尔雷奇(A.R.Orage)
我策划本书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做了一个梦。梦中有卡罗勒斯·奥德菲尔德(Carolus Oldfield)、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1907—1990),以及一个穿着白外套的男子(我当他是研究科学的人或实验室的技师),三人正指着一件仪器在争论。那仪器看起来像是脑电图仪(EEG),因为仪器上有电极头,可以接在受检测者的头皮上,还有电线连接着记录笔,在滚筒转出来的纸上,画着有尖锐起伏的记录曲线。但是卡罗勒斯说那是一架“诗的机器”。隔壁房间有位年轻的女子在唱歌,我受歌曲的纯朴之美感动而醒来。这梦是什么意思?这些人为什么在我即将提笔写书之前在我梦中出现?梦中的人又为什么说脑电图仪是诗的机器?读者也许很想知道梦中的这几位是何许人也。
卡罗勒斯·奥德菲尔德是我于1950年代先后就读的两所大学——瑞丁(Reading)和牛津——的心理学系教授。他是位亲切而对学生倾囊相授的好老师,我懂得用科学方法研究心理现象,大多来自他的教诲。我修毕医学课程后,他又鼓励我根据在雅典梅特拉婴儿中心研究婴儿依恋行为的结果作博士论文,并且请约翰·鲍尔比指导我,鲍尔比同意了。
当时我是初出茅庐的心理分析师,这样的安排是天赐的良机。鲍尔比先前发表了母亲与子女情感联系的研究,不但广受国际推崇,而且促成了心理分析理论的变革。我能适时受教于他这样的良师,何其有幸。他最令我景仰的是将心理分析带入生物科学主流,实现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愿。可惜响应热烈的分析师不多,一般人仍是言必称祖师爷的神圣经典——虽然它已威信大减。结果是,心理分析一直带着宗派色彩,不像一门科学。
我拥护荣格(Carl Jung)学说的立场虽然与鲍尔比的不同——他是受克莱因(Melanie Klein,1882—1960)学说熏陶的,我将荣格的理论与他的“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相连,并且与动物行为学(ethology)并论,却获得他的支持。我于1982年发表第一本探讨这个议题的书《原型:本我的自然史》(Archetype:A NaturalHistory of the Self),也得到他的热切回应。这都是令我铭记于心的。
我回想梦的内容,明白这是因写书的准备作业引起的。这梦要表达什么讯息呢?我觉得它在提醒我谨记奥德菲尔德和鲍尔比象征的科学传统,同时又告诉我,梦的创造者是一位诗人。隔壁房间的年轻女子乃是荣格派任何男性分析师的常在伴侣,是他的安尼玛(anima),他的女性情结,为他在潜意识沟通中斡旋。她是站在爱欲(Eros)、音乐、诗、生活那一边的。荣格曾说:“安尼玛乃是生命的原型。”她唱的歌是要点出卡罗勒斯给我的讯息。
穿白外套的男子在我梦中忙着操作“诗的机器”,以保持记录正确。过去四十年中,以科学方法研究梦很倚重脑电图仪,第四章会再谈到。脑电图仪记录提供了极重要的资讯。可惜的是,有关解读梦的著作都不大重视这些研究记录。以梦为题的科学研究书籍大都把焦点放在神经生理学上,很少提及心理层面,而且往往认为心理因素无关紧要。这种短视的看法如今已不可取了。
解梦学(oneirology)发展至今,再要把梦当作纯粹心理学或神经生理学的现象来讨论,都是行不通的。显然梦既是心理现象,也是神经生理学的现象。我们必须往整合心理学及神经学两方面既有知识的路上走,才对梦的研究有益。梦原是心理的活动过程。而我希望证实,梦的起源与人类这个物种的进化历史之相关。不逊于与个人经历之关系。
正当心理分析欠稳固的科学基础招致各方批评的时候,我们刻意用系统化方法研究梦,格外具有意义。近年来弗洛伊德的科学威望暴跌,染有浓厚弗洛伊德色彩的各派心理治疗法都遭受严重打击。因此,对我们这些为心理治疗的前途着想的人而言,当务之急即是将假设构架为可测试的型态,说明我们的实际做法,以便世人公开评估其合理性。同时我们也应切记,会做梦的大脑不只是负责“处理资讯”的一个电化学系统而已,就算它是一部机器,也是一部“诗的机器”——卡罗勒斯对我梦中那部脑电图仪的说法,这样才是对科学有益的。心理治疗和梦的解析都是——也永远会是——艺术成分甚于科学的,我们把研究工作放在可检证的立足点上之后,没有必要舍弃个人的治学宗旨与长久经验培养的洞察力、同情心与见识。
自我走入心理学的专业生涯以来,一直怀有的抱负是:为成就条理清晰的人类本性的学说贡献一份力量。在鲍尔比的影响之下,我渐渐明白,必须用比较的方法,将深层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演化生物学、社会科学、人类学的数据资料汇整,才可能规划出这样的理论。梦的比较研究是达成这目标的根本要件,因为,梦使我们与人类自古以来的关怀产生直接的联系——这一点也是我希望能证实的。如今,心理学、分析方法、动物行为学、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都已经相当进步,可以综合其成果,开启解梦学史上可能是最令人振奋且具有创意的时代。
20世纪后五十年的各项发展之中,动物行为学的革命和脑电图的研究,使我们对于梦的本质及功能的理解彻底改观。这种改变也大大有助于肯定荣格在本世纪提出的临床直观:人类血源的根本相通,不但从身体和基因可以明显看出,而且流露于我们的神话、梦境、精神病症、工艺品。从儿童的游戏和语言能力,从各个文化中的人们都喜爱的故事和叙事诗歌,从人人随时感觉需要做的仪式行为、歌唱、吟诵、舞蹈,都明显可见人类发展所依凭的基本结构——荣格称之为“集体潜意识的原型”。人类学、精神病学、神经医学.深层心理学。都能导引我们领悟这深层的原型真实如何影响个人的现实面。荣格称这深层的真实为“两百万岁的本我”,认为它必然蕴含在我们做的每件事、说的每句话、转起的每个意念之中。这个从远古留存下来的元素,在我们做梦时最为活跃。神经系统科学的研究也证实,梦使我们与大脑中最古老的结构相连。我们每天夜晚进入一个神话的疆域,一个原始的迷宫,那儿居住着我们先祖的鬼魂和众神祗。我们从那儿撷取人类的古老智慧。梦中的鬼神往往以现代的相貌出现,我们的梦拿这些人物编排新的神话,其实那只是改穿时装的人类旧神话。这个原始的本我正是人类演化遗产的体现,也是梦的根本生命力。
我梦中的人有两位(卡罗勒斯和约翰)是我认得的导师型人物,是荣格所说的“智慧老人”的化身。第三个人——穿白实验衣的男子——又代表什么呢?我思索了一阵才明白,他是代表现代的“英雄”人物,一位纯科学的研究者,一心一意要用实验方法或以可复制可证明的数据为依据的逻辑演绎的方法来开拓新知。在梦中遇见不认识的人,可以想象自己和他对话。我和他交谈后发现,这位科学家认为梦是无聊的猜谜游戏,都是可以用神经化学解释的。我告诉他,他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从不把自己的梦当作真实的心理活动看待过,没法亲自领会它。只要他肯和自己的梦密切联系,很快就会发现梦的意义有多么丰富。他却没好气地回答说:他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上。
从事梦的神经生理学研究,却否认梦的心理学意义,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他们就好像只关心电视机科技,却对播出节目不感兴趣的工程技士。一般不是专门研究梦的人,大概不至于对梦不屑一顾,但有许多人会把梦当作电视机——摆在房间一角开着,却不注意看它,对于播出节目的内容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他们既不清楚节目内容,也就懒得花时间去留意,心态和我梦中那位科学家一样。但这无异于暴殄天物,因为梦也是一种资源,弃之不用只会造成自己的损失。梦带我们走进人类经验的深层。可以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也能使我们更敏锐地自觉活着的意义。梦不是只有受过高度专业训练的分析师才能懂的神秘现象。我要在本书中证明,只要是真心想学的人,都能学会这样一门艺术,善用梦的功能。
因为做梦的状态对于人类各式各样创造活动都有助益,本书的探讨范围自然相当广泛。第二、三章从史书最早的梦境记载讲起,逐步讨论各种理论之形成与演变,以及从狩猎采集时期直至现代的各种解梦方法。第四章检讨梦的科学研究,按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麦克莱恩(Paul MacLean)的大脑三体(triune brain)的神经学论点、埃德尔曼(Cerald Edelman)的记忆与意识的“神经系统达尔文主义”主张等进行析论。第五章概述荣格的原型概念和情结概念,并且就生物学观点检视它们如何影响梦之形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