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无心之举
晚冬的一个寒冷的下午,在纽约市中心,妈妈拉着我的手往华盛顿广场公园走,当时我只有6岁,非常淘气,狂爱蜘蛛侠、鲨鱼、恐龙、体育运动,让父母头大不已。“这孩子太能折腾了,”我妈妈总会这么说。我总是会缠着爸爸玩足球或棒球,或者在卧室里和他摔跤。朋友们称我是“皮肤杀手”,因为在操场上玩金属棒或潜水时膝盖总会皮开肉绽。起初我对极限小轮车产生了兴趣,用隔壁建筑工地上的木屑和煤块建成了临时车道。我一向不肯戴头盔,直至有一天因为一次大的扭伤最后做了一个面部植皮,以至于妈妈下了狠心,除非我听话,否则骑马时她也不戴头盔。
这段路我们走了很多遍了。我喜欢在猿猴丛林中荡来荡去,像人猿泰山那样,丛林就是我的天地。但现在,事情有点不同了。当我转过头时,大理石棋盘上一个个神秘的小塑像令我非常惊讶与好奇。当时的感觉就像是自己在窥探丛林,棋子就是各种动物,充满魔力,随时要跳出棋盘。两个公园常客坐在棋桌两边,互相调侃对方。气氛异常紧张,之后就见一枚枚棋子开始出动,他们灵活地移动着棋子,快如闪电,精准神速,黑白两道占据棋盘,阵营分明。我被这一战场深深吸引住了,觉得这个游戏似曾相识,我喜欢它。紧接着就有一群人围了过来,我没能继续看下去。妈妈轻轻地拉起我的手,继续往前走去。
几天后,我和妈妈又经过了公园的这个角落,我松开妈妈的手,朝着一位有银灰色胡子的老人跑了过去,他正在其中一张大理石桌上摆着塑料棋子。那天我曾在学校里看到有些小孩子在下象棋,我觉得我也能下。“想玩吗?”那位老人透过眼镜疑惑地看着我。妈妈马上道歉,解释说我不会下,但老人说没关系,他也有小孩子,也比较空。妈妈告诉我说,在下棋过程中要把舌头伸出来,抵在上唇上,言下之意就是要么放弃要么就专心好好下。当时的感觉很奇怪,仿佛找到了自己遗失的记忆。移动棋子时我感觉自己以前也这样做过。这个游戏,就像一首好歌一样,非常协调。我在思考下一步要怎么走时那位老人就看会儿报纸,但几分钟后他就开始愤怒了,推开我妈妈,说她不该推他。很显然,我的棋下得不错。
在对几个棋子的布局进行协调后,我发动了一场进攻,那位老人不得不全力反击。过了一会儿来了一群人围在了桌旁,大家都在窃窃私语,说着“年轻的菲舍尔”之类的话。妈妈有点云里雾里的,不知道她的儿子干了什么。我陶醉在自己的世界中,最后老人赢得了比赛。我们握了手,他问了我的名字,写在报纸上,并说:“乔希?维茨金,有一天我会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
从那天起,华盛顿广场公园成为我的第二个家,而象棋也成了我的最爱。放学后我不再急着去踢足球或打棒球,而一心想去公园。我会对着某个看着有点吓人的家伙坐下,摆出比赛的架势进入战斗。我喜欢比赛的刺激,有时我会不停地玩快棋,连续几个小时盯着棋子看,不断思考战术,来来回回摆弄着棋盘的布局。回到家脑子里总是在想着下棋这回事,接着就会让爸爸把他尘封已久的布棋盘拿出来跟我玩。
慢慢地,我成了公园的常客,他们开始保护我,向我展示下棋的技巧,教我怎么发动致命一击,直接让对手落败。我成了这条街上的宠儿。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个很古怪的学堂,周围的观众有酒鬼、无家可归的天才、赌徒、吸毒者、另类艺术家等,他们粗鲁、聪明、颓废,住在贫民窟里,却对象棋充满了热爱。
每天,除非下雨或下雪,华盛顿广场西南角的19张大理石棋桌旁都会出现这些人的身影。大多数时候我都会在那儿,用小小手臂拿着棋子,嚼着口香糖,从比赛中学习象棋。父母在同意我来公园之前也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的,但我很倔,而且在我来下棋时那些人也都很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他们熄灭了香烟和大麻烟,说话收敛了很多,不正当交易也明显减少。我总是坐在他们中间,一坐下就聚精会神,开始鏖战。妈妈告诉我说,她看到她的儿子在下象棋时就像是一位老人。我太过于专注,以至于她觉得如果她把手放在我眼前的话都会燃烧起来。为什么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会对象棋这么认真,对此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可能这是一种本能吧。
几个月后,我已经击败了许多下了几十年象棋的人了。每次输的时候,就会有朋友给我提一条建议,比如“乔希,你进攻太少了,让对方一点危机感都没有。你得发动进攻,让对手恐慌起来”,又或者“乔希,你得护住王和车,不护好本营会让你很快败下阵来的”。之后我会马上击钟,摆好棋子重新开战。每次失败都是一个教训,每次胜利却是一次喜悦。每天象棋都让我爱不释手,乐在其中。
只要我来下棋,总会有一大群人过来观战。我成了这个小小世界中的明星了,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能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很让我兴奋,但同时也是不小的挑战。我很快就意识到了,当我脑子里在想着有人在观战的话,我的棋就会下得很糟。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想忽视身旁大人们对自己的评论真的很难,我似乎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棋盘布局的紧张气流与周围的议论声、交通噪音、救护车的警报声,所有这些都形成了一个激人奋发的强大漩涡,开拓自己的思路。有时我在华盛顿广场的吵闹声中甚至比在安静的卧室里更容易进入状态,但有时我会环顾四周,看着身边每一个人,因他们的谈话而分神,下得一败涂地。我相信我爸妈最开始在旁边观看我下象棋时一定很沮丧:他们根本分不清我是在嚼软Q糖、微笑、开玩笑、考虑自己的棋局还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中。
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在和朋友杰瑞下快棋时,有一个高个子站在人群中看。我注意到他了,但马上投入到了比赛中。几个小时后,他找到我父亲,并自我介绍说他叫布鲁斯?潘道菲尼,是国际象棋大师和象棋老师。布鲁斯告诉我父亲说我很有天赋,他愿意教我。
我父亲认出,在1972年历史性的鲍比?菲舍尔vs鲍里斯?斯帕斯基的世界象棋大赛上,就是布鲁斯与舍尔比?利曼一起做的电视解说。这场比赛是对国际象棋的大革命,这是冷战期间的一场大赛,矛头直指前苏联世界冠军,他的背后是一支百人教练与陪练团队,而发起挑战的却是一位性格怪异的美国人,他所有的应战准备工作都是独自在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菲舍尔兼具詹姆斯?迪恩与葛丽泰?嘉宝的风采,让全美为之着迷。
两大高手此次对决的政治气息极浓,随着比赛的深入,它逐渐被视为冷战的象征。亨利?基辛格给鲍比打电话加油,双方政客也紧密关注着每场比赛。舍尔比与布鲁斯每天在电视上做深入浅出的赛事分析时,全球人都屏住呼吸观看比赛。最后菲舍尔赢得了比赛,他马上成了国际名人,而象棋也在全美风靡起来。瞬间,这项活动取得了与篮球、橄榄球、棒球、曲棍球同等的地位。之后在1975年,菲舍尔放弃了卫冕赛退出了人们的视线。自此以后,美国的象棋界一直在寻找另一个鲍比?菲舍尔,让这项赛事重新发扬光大。
舍尔比和布鲁斯的解说令父亲二十年来一直记忆犹新,而现在,布鲁斯主动要求教授他6岁的孩子。我有点不知所措,象棋是挺好玩的,公园里这些人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把我教得很好,所以为什么我还要再多一位老师呢?我把象棋看成了自己的隐私,它是属于我自己的既亲密又充满狂想的世界。要想进入这个世界,必须要得到我充分的信任,而布鲁斯要想教我也必须先要克服这个问题。
我们最开始的课程并未按常规进行,我们几乎不是在“学习象棋”。布鲁斯知道最重要的是要先互相了解对方,建立起真正的同志情谊,所以我们会谈到生活、运动、恐龙这些让我感兴趣的事。但只要一谈到象棋,我就会坚守自己的想法,拒绝接受任何正规的指导。
我一直坚持着自己在公园里学来的一些坏习惯,比如,早早出“后”。这是初学者的一个典型错误:“后”是棋盘上最具威力的棋子,因此大家都想马上让她投入战斗,发挥威力。如果和那些没有技巧、连简单进攻都招架不住的对手比赛时,这个战术非常有效。但问题是,“后”要想和对手的棋子对决的话必定损失惨重,所以她就会在棋盘上被迫着走,而对手自然会出动价值相对小一点但威力十足的棋子对孤军作战的“后”发起猛烈进攻。道理很明显,但我就是不听,因为之前我这样做也赢了不少比赛。布鲁斯只凭这样说无法让我信服,他必须得证明给我看。
布鲁斯决定和我下一场快棋,就像我常常在公园里下的那种。我犯了某个本质错误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我违反了哪项原则。如果我拒绝改变,他会紧接着利用我的失误,直到我的棋局七零八落。慢慢地,我认识到了布鲁斯理念的正确性,他逐渐赢得了我的尊重。我的“后”开始等待正确时机再出动了。我学会了如何布局,如何控制中心地带,如何有系统性地发动进攻。
赢得我的信任后,布鲁斯开始正式教我,并允许我表达自己的想法。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太过急躁。我是一个极具天赋与本能的孩子,曾击败了众多没有接受正规训练的街头棋手们。现在是时候让我放慢脚步,约束自己的直觉,而布鲁斯对此也有自己的一套。他知道如何教会我更懂得约束自己,同时又不减弱我对象棋的热爱或是压抑我内心的想法。很多老师都不懂得这种平衡状态,而是逼学生采取某种固定模式。多年来,我曾遇到过很多这样自以为是的老师,也逐步意识到,从长期来看,他们的这种做法对学生有极大的杀伤力,无论是哪套模式,在我身上都不管用。
我知道自己的确挺难管的,我的父母培养出了一个任性的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鼓励我参与在家中举办的激烈的晚餐会辩论赛,讨论艺术与政治。他们教导我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也要考虑别人的想法,而不要盲目地追随权威。幸运的是,布鲁斯的教育理念非常契合我的性格。他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博学之人,更多地是把自己当成是我成长过程中的向导,而非权威。如果我与他意见不一致的话,我们就会面对面进行探讨,而不是单方面的训话。
布鲁斯通过提问的方式让我放慢速度。每当我要做一个重要决定,无论好坏,他都会要求我解释自己思考的整个过程。要达到这个目标有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否意识到了对手的威胁呢?有没有考虑过不同的布局顺序呢?布鲁斯不会一味地庇护我——有的老师为了避免自己太过独裁,会表扬所有小选手的决定,无论是好是坏。他们的本意是打造信心,但相反的,这样做只会打击小孩子的客观性,鼓励自我纵容,或许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他们创造出老师和学生间的不诚实的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一个聪明的孩子都能够感觉出来的。
当我走错了一步,布鲁斯就会问我是怎么想的,之后帮我找到不同的解决方式。课上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沉默中度过的,两个人都在思考。布鲁斯不想给我灌输过多信息,而是帮助我的思维逐步走向成熟。慢慢地,通过他劝诱式、幽默、轻描淡写的教学方法,布鲁斯为我打下了根本性的象棋理念根基以及对于分析、计算的系统化理解。尽管这些新知识非常宝贵,但最初几个月的学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布鲁斯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象棋的热爱,并且从未让技术性的东西影响了我对象棋的内在感觉。
在最开始与布鲁斯一起合作的日子里,我们会每周在我家见一至两次,有时是早上,有时则安排在放学后。而其他大部分时候,我会到华盛顿广场和朋友们在公园中切磋一下。在六七岁时,我的象棋教育有两大来源,关键就在于如何让它们和谐共处——街头鲁莽的棋童不得不与布鲁斯所栽培的、经过专业训练并且有耐心的棋手合二为一。我非常喜欢欣赏以前世界大赛无与伦比的魅力,我总和布鲁斯一起研究,有时静静地坐着,用上20分钟计算象棋残局的布局会让我兴奋不已。但也有些时候,认真思考也会让我感觉很无聊,我宁愿去和好朋友下快棋,发动进攻,有点鲁莽行事,创造出美丽的混合风格。公园总是很有趣,毕竟我还是个小孩子。
我的父母和布鲁斯一致决定,我至少得过个一年左右才能参加比赛,因为他们希望,在我与象棋的关系方面,学习与激情排第一位,竞争只能在第二位上。我妈妈和布鲁斯对于让我置身于象棋的巨大压力中甚感矛盾,他们想让我多过几个月天真无邪的日子,这让我心存感激。当我最终开始参加学校比赛时,我刚过7岁生日,感觉比赛比较简单。和公园里那些人一样,与我同龄的小孩子根本不懂得复杂的进攻和防守战术,并在压力中败下阵来。有的小孩子一开局时会布下几个很有威胁性的陷阱,心里记下在哪方面会有机可乘,所以我经常在开局时会丢一两个兵,但之后他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对我来说,极具竞争性的象棋并不是一项追求完美的项目,它更多的是追求胜败,两个对手互相把握优势,轮流占领上风。我在华盛顿广场的朋友们都是很勇敢的竞争者,你永远都无法把他们排除在外,事实上,在处于困境时他们才最具威胁性。许多很聪明的小孩子期望能顺利获胜,而当遇到麻烦时,他们马上就慌了手脚。
我总能在不利局面下翻盘。我的风格是让比赛变得复杂,然后以我的方式走出混乱局面。当棋局比较乱时,我的信心就非常强。布鲁斯和我也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残局,也就是在几乎空了的棋盘上,将高水准的象棋准则与深层次计算融合起来,创造出令人犯难的局面。如果我的对手想在开局就获胜的话,我就会布局,进入复杂的中局和捉摸不透的残局。所以,在比赛进行过程中,他们的自信心会逐步减弱,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的手中了。注意到这些趋势后,布鲁斯开始称我为“老虎”,直到现在他依然还这么叫我。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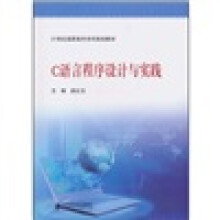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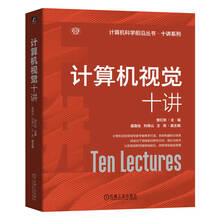





——卡尔·瑞普肯,巴尔的摩金莺棒球队,2007年棒球名人堂
这完全是维茨金对“精通”一词的深刻理解。这趟旅行物超所值。
——吉姆·罗尔,运动及潜能发展研究所CEO,《全神贯注的力量》作者
我意识到自己最擅长的既不是象棋也不是太极,我最擅长的是学习的艺术。
——乔希·维茨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