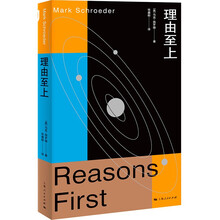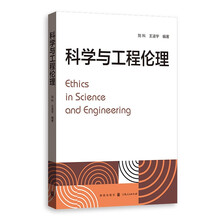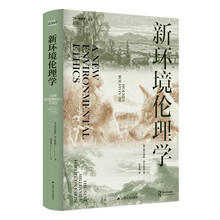第一章 仁的科学
安敦·冯·罗文霍克(Anton Van Leeuwenhoek)改变了我们对于自然界的看法。1632年,他出生于荷兰的德尔福特(Delft),他的家庭主要以酿酒和编筐织篮为生。他过着平静的生活,先后当过织布工人、市政府小官员和葡萄酒质量检验员。晚年,他开始手工研磨镜片来制作简易的显微镜,以便把自家商店里的葡萄看个清清楚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把附近湖泊里的水藻也放在他那架三四英寸的单透镜显微镜下。他还观察了鱼的细胞、他本人的精液,还有两个从未清洁过牙齿的老年人的牙斑。他是研究细菌、血细胞和精子的第一人。他打开了人类的眼界,看到了微生物的世界,并由此改变了人们对“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理解。
本书提供了一个达尔文式的透镜,透过它我们可以了解有关积极情感的新兴科学。我们把这门新学科称为仁学,以此纪念孔子提出的“仁”的概念。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指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人性和尊敬等。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的中国,孔子摒弃了暴力、物质主义以及等级森严的观念,大力宣扬“仁”的思想,通过这种方式,孔子教给人们一种发现有意义的生活的新途径。孔子说,仁人志士应该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所以,在你从别人身上引发出仁善的同时,你自己也会感受到深刻的满足,此时此刻你就体会到了“仁”的含义。
“仁”的科学基于其自身对于事物进行显微镜式的观察,在此之前,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得到过人们切近的省察。其核心在于,“仁”的科学基础建立在情感之上,比如同情、感恩、敬畏、尴尬以及自得其乐之类的情感。这些积极情绪在人与人之间不断传播,成就了人们彼此之间的美好感情和善意。“仁”的科学用它的显微镜研究了一种新兴的人类语言,即面部肌肉运动的语言,这种语言传递着忠诚的信号,肢体接触的定式传递了感激之情,玩笑的口气则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它把构造我们自身的新生物质聚焦于我们注意力的焦点之上,把焦距瞄准神经传递素以及促进信任、关怀、忠诚、宽恕和游戏的各个神经分区,进行清晰的精确观测。它发现了有关人类性善的进化历程,其做出的崭新思考修正了人们长期信奉的理论假设,即我们的神经结构完全是为了达成欲望的最大化,为了相互竞争,为了加强我们对于恶的警惕性而形成的。
如果先戴上这副达尔文式的“仁”的科学眼镜,然后再来打量这个世界,你的“仁率”(jen ratio)很可能就会因此而得到改善。“仁率”的指标是一个观察你生活中善与恶的平衡的透镜。在仁率的分母部分,请你放上最近你见到的那些与人为恶的行为,这种行为给他人造成了恶劣影响。比如说,一个盛气凌人的驾车人在飞驰而过时把你撞倒在地;傲慢自大的用餐者在昂贵的饭店里嘲笑那些穿着不大考究的食客。在这个分母的上方,即仁率的分子部分,我们要填报的是那些成人之美的行动。比如说,在拥挤的地铁中一只仁慈关爱的手放在了你的背上;一个穿着游泳衣的老年妇女,当她神经紧张地把脚尖放到游泳池时,一个小孩却向她投来了欣赏与赞美的目光;当陌生人不小心踩到了一位女士的脚时,她却报以欢乐的笑声。当你的仁率上升时,你所处的世界中的人性因素也就上升了。
让我们赋予仁率一个小小的生命吧。在我的女儿们放学后的操场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在仁率的分子部分:两个男孩子笑着,互相搔乱对方的头发,女孩子们则在做倒立或者玩侧手翻。当看到哪个小伙伴不小心摔了个大屁蹲时,他们就会哈哈大笑。在柔软的草地上,孩子们在一个小男孩身上玩叠罗汉,这孩子很兴奋地把橄榄球抱在胸前不放。同时,在分母部分:一个男孩拿走一个更小的男孩的鞋子来逗他玩;两个女孩子悄悄耳语着,对另外一名要参加她们的独角兽游戏的女孩品头论足。在操场上的这个活动场景中,所表现出的仁率为3/2,或者等于1.5。这是一个相当良善的场景。在漫长的排队等待购买邮票的八分钟里,我看到了表现恼怒的24种不同形式,从叹息到怒目而视,再到令人生畏的呻吟,然而同时也有一个人连笑了三次。此时的仁率为3/24,即0.125。
你也可以把仁率应用到任何领域:我们的内心生活、婚姻生活美满或出现危机的不同阶段、家庭团圆聚会的过程、街坊邻里间的关系、总统的言辞、各个时代的精神。如果我们把仁率当作一个透镜,那么,透过它你就可以思考一下,为了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仁率以及国家的健康
只用简单的指标就可以有力地判断一个人的健康状况。阿普伽新生儿评分(指对新生儿的肤色、心率、反射应激性、肌张力和呼吸力五项的评分)、血压指数、情商指数都只需要几分钟时间就能得出结果,但是它却可以揭示人们要用一生才能走完的路程。对于当代社会的健康状况,人们又可以用什么方法加以诊断呢?难道说是杀人犯罪比率?或者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或者是社会财富在贫富两极的分配状况?还是那些相信人能复活的公民所占的百分比?抑或是人们嘲笑荷莫·辛普森动画电视剧集《辛普森一家》中的主角,后被搬上了大银幕。——译者注(Homer Simpson)的速度?假如我拥有一个标尺来测量个体、婚姻、学校、社区或者文化的社会福利,那么我将选择仁率作为我的指标。
对于个体而言,新的研究发现,较高的仁率即那些旨在成人之美的努力,才是抵达有意义的生活的必由之路。如果你每周参与五个慈善活动,比如说献血,或者给朋友买一个圣代冰淇淋,或者给穷人捐钱,这些活动有助于提高个人的长期福利。你在别人身上花的20美元(或者捐赠给慈善事业),将比你把同样的钱花在自己身上更能提高幸福感(即使大多数人认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才是抵达幸福的可靠的途径)。在残酷无情的经济竞争中,人们相互给对方留下了累累伤痕,但是,那些精诚合作者和原谅合作伙伴的自私自利企图的人,一定比那些只知竞争的人更为成功。新兴的神经科学表明,我们天生是向善的。当我们给予别人时,或者与别人合作的时候,大脑的犒赏中枢,比如说富含多巴胺受体的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就被激活了。比起接受,给予更能为自身带来更多的福祉。
个体生活的状况与婚姻生活的状况相似。成就配偶之善(而不是恶)会带来许多正收益。在婚姻生活中,一个最为有害的发展是低仁率的出现。在20多项有关配偶如何解释对方行为的研究中,那些行将离异的夫妻往往把婚姻生活中的美好瞬间归因于对方的自私动机(比如说,“他给我送上鲜花,是为了讨好我,好让我参加他周末的高尔夫球赛”)。遗憾的是,他们往往把那些争吵、武斗和危机的责任也归罪于对方(比如说,“如果她时常能够清扫一下我家汽车的后座,那儿就不会发霉长毛了”)。幸福的婚姻则往往由较高的仁率所主导:他们慷慨地赞扬配偶,并且在对方的疏失中看出其潜在的美好品德。
仁人(Jen Yen)
最近有关社会福利的调查研究可谓层出不穷。种种迹象表明:在美国,仁的丧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在美国人中,信任本国同胞的国民比例在过去的15年中已经降低了15个百分点。美国文化的健康状况堪忧。许多症候如社会混乱的感觉不断攀升,孤独感与日俱增,婚姻幸福感逐年降低,这些指标都在不断恶化。今天,美国的成年人在他们亲友中拥有知己的数量比20年前减少了1/3,小宝贝们与折叠式婴儿车的肢体接触远多于来自父母双手的抚摸。最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21个工业化国家的研究表明,美国儿童在总体福利方面的排名仅仅位居第20位。
一提起美国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滑坡,人们就会抱怨说,这是因为美国在高等教育中放弃了西方文明的经典、道德相对主义盛行以及宗教信仰的缺失。还有人散布谣言,试图解释我们的社会构造在内耗方面的各种原因:谦虚作风的消失,性早熟,交际媒介的增生与扩散,还有快餐文化。
我认为,这些令人担忧的社会趋势体现了更为广泛的关于人性意识形态走向末日的紧迫状态,而这种状态的仁率正在向零逼近。这种意识形态不乏极具影响力的支持者,从弗洛伊德到众多进化论者,莫不如此。在经济学院系的殿堂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个观点最强大的支持者。他们对于人性做出了品格鉴定,即人们耳熟能详的理性选择理论。这个理论逐步渗透、延伸到了进化论思想、心理学以及我所做的情感研究的诸多领域。然而,它也常常遮挡住我们看待这门科学与实践的视线。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经济人”假设,它把经济人作为人类进化的最新阶段。最初,哲学家们原本用经济人这一概念来描绘原始人类的情形,在这些哲学家中间就有大名鼎鼎的亚当·斯密。产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财富的扩张和科技的进步让他们震惊。居于首要地位的假定是:经济人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的每个行为都要以促进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为宗旨。这种个体利益可以表现为个体所享受到的快乐、个体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进化论者心目中,这种个体利益还包括了个体基因的散播。
1954年,当人们在所谓脑膜的脑部边缘地带第一次发现了“兴奋中枢”时,科学家发现:小白鼠在既不饥又不饿的情况下,会连续数小时不间断地推动前面的横木,目的只是要获得足够的刺激,以使那个脑部区域保持亢奋。经济学家们由此做出的假设是:如果你我和那些小白鼠有许多共通之处,那么,我们的神经构造也是为了持之以恒地追求个人满足。这样一来,今天我们就有了神经经济学这个全新的领域,它正在为此提供科学证明:在人类大脑长达60英里的神经系统线路中,那些对各种基本感觉犒赏作出响应的各个神经区域,例如体验味觉香甜的犒赏神经中枢、体验嗅觉馨香的犒赏神经中枢,以及在金钱唾手可得的兴奋状态下的犒赏神经中枢,在核磁共振成像仪下面它们会熠熠生辉,亮光频闪,犹如圣诞节的烛光一样明亮。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