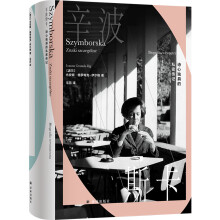一种私生子身份的戏剧
也许正是通过其戏剧作品,萨特才真正变得“大众化”起来。戏剧的确是他作品中看似最易被接受的部分。当然,这并不全然意味着它最能被大众理解,但至少与随笔和纯哲学作品相比,戏剧对于许多人来说更加通俗。此外,可贵之处还在于它们阐释了几乎所有萨特式的主题,并将之搬上了舞台。当然,对他作品中的小说部分我们也同样论及颇多。但这部分的不足在于,《自由之路》这部作品仍未完成。(除了两个片段外,第四卷尚未出版,我们担心它永远也不会面世。)如果考虑到萨特本人对这部小说不甚满意朋态度,以及他站在每一部剧作的实践者中间,对自己的戏剧创作明确给予的总体上的偏爱,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要了解萨特思想的主要演变过程,立足于戏剧方面似乎更为合适。
萨特定义了另一种戏剧门类,并将其视为当今时代惟一可行的剧种——“境遇剧”(theatre de situations)。它既不同于悲剧,也不同于心理剧。“人在既定的境遇中是自由的,人在此境遇中自由选择,在境遇中自行选择,同时又是通过境遇进行选择。如果以上属实,那么就必须在戏剧中展现简单的、充满人性的境遇以及自由,而后者正是在境遇中被选择的……戏剧所展示出的最动人之处,就是一个处于自我塑造过程中的性格,选择的时刻和自由决定的瞬间。这个决定约束道德,并贯穿人的一生。就像只有把所有的演员集中起来才能完成戏剧一样,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具有总括性的境遇,使之为大家所共有。我们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比如结舄。方式,暴力的合法性以及行为的后果,个人与集体、个人的事业与历史的恒定关系,还有数以百计的问题。在我看来,戏剧家的任务就在于,从这些受限制的境遇中选择最能表达忧思的境遇,并将其作为针对某些自由而提出的问题呈现给大众。”
因此,“境遇剧”也就相应地成了自由的戏剧。这便出现了两个主题,也可以说,出现了同一主题的两个方面:境遇中的自由。这也正是我们从萨特的第一部剧作——“三幕剧”《苍蝇》中所发现的。
俄瑞斯忒斯,时年二十,是阿伽门农和克吕泰墨斯特拉所生的儿子。在家庭教师的陪同下,他回到出生地阿耳戈斯城。当年,阿伽门农遭克吕泰墨斯特拉的情人埃癸斯托斯谋杀,三岁的俄瑞斯忒斯被驱逐出城,后被雅典的富翁收养。他周游列国,博览群书。他的老师告诉他:“无论如何,人们的风俗习惯不尽相同。”因此,他学会了透过一切事实的假相,靠主观进行判断。总之,他“从小就开始训练具有怀疑主义性质的、诙谐的性格”,并从众人身上获得了宝贵的财富——“精神自由”。所有这些就如同家庭教师对他的评价一样:“您年轻、英俊而富有,并且像老人那样深谋远虑,能够摆脱一切羁绊和信仰,没有家庭牵累、没有祖国、没有宗教信仰、没有职业,无拘无束,同时也明白自己永远不要让自己受到拘束。总之,您高人一等……”
然而,俄瑞斯忒斯对令人仰慕的命运并不满足。他来到阿耳戈斯,站在父亲的宫殿前。在他的宫殿前,首先触动俄瑞斯忒斯的,是他深切地感到这座宫殿并不属于他自己,仿佛是第一次看见。说得深一些,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回忆,什么也不归他所有,他不属于任何地方,于是自己什么也不是。“……你给了我自由,蜘蛛网上的游丝已被风吹断,在离地面十英尺处飘荡着,可我轻若游丝,在空中漂泊为生……我是自由的,谢天谢地,啊!我多么自由自在,我头脑中一片空白,妙不胜言。”“我勉强生存着……我领略过幽灵的爱,这种爱就像蒸汽那样轻薄,游移不定;但是我不知道活人的强烈激情……我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对别人来说,我是个异乡人,对我自己来说,我也是个陌生人。这些城市在我的身后关上了城门,犹如静静的流水……”
在他降生的这座城里,俄瑞斯忒斯感到被排斥在外:那酷热是属于别人的,阿耳戈斯晚间凉爽的阴影将洒满大地,那晚问的阴影也不是属于他的。因而,他回来后做了一个梦。他梦见用武力进入这座城市的深处,夺回了王位,并最终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啊!你看,如果这是一种天职,一种赋予我对他们行使统治权的神圣职责,如果我,即使是通过犯罪,能够夺走他们的记忆、恐怖和希望来填补我心头的空虚,哪怕是杀死我自己的亲生母亲,我也……”
……“哪怕是杀死我自己的亲生母亲……”,如此简单的叙述方式。当然,在做了片刻白日梦之后,俄瑞斯忒斯还是决定再次离开:“看看是否有人供给我们马匹,我们可以策马直奔斯巴达,我有一些朋友在那儿。”他并没有考虑厄勒克特拉,他的姐姐,那个即将出现并激励他实现梦想的人——甚至她脱口而出的、不谨慎的言语,也是一种激励。厄勒克特拉非常清楚自己与他的命运截然不同:她在父亲的王宫中长大,但在那儿,她却成了母亲和篡位者的臣仆。她因此生活在反抗与仇恨之中。十五年来,她等待着弟弟的归来,梦想有朝一日他能回来惩罚这两个凶手,拯救阿耳戈斯的百姓。因为她懂得必须诉诸武力:“我们只能以毒攻毒。”而事实也是如此,阿耳戈斯的人民亟待拯救……
而那些苍蝇,数以百万计的苍蝇,十五年前就降临到他们头上了。它们是神派来的,象征着自埃癸斯托斯弑君以来一直笼罩在整个城市上空的悔恨。
俄瑞斯忒斯 埃癸斯托斯悔恨了吗?
朱庇特 埃癸斯托斯悔恨?我觉得,他若悔恨,这才怪哩!不过,这倒无关紧要。全城上下都在为他忏悔,这种忏悔是有分量的。
凶手统治着这座城,毫无悔意地统治着。然而他的统治却是凌驾于他人的悔恨之上的。
俄瑞斯忒斯 ……我原来还以为神祗是公正的呢。
朱庇特 唉,不要动不动就诋毁神祗。难道任何时候都得施以惩罚吗?把这样的淫乱转化为法治,岂不是更好吗?
写到这里,我们想起《苍蝇》的首演是在德国占领时期。剧中对时局频繁的影射,尤其是对维希方面领导执行的认罪政策的影响,在当时看来比在今天更为明显。“……正当我们要陷入悔恨之时,维希政府与他们的合作者试图把我们从中推出来,但又压制着我们。所谓占领,不仅仅是胜利者在我们的城市长久地驻扎,而且还出现在所有的墙壁和报纸上。这肮脏的画面就是他们想要我们施于自己身上的。开始时合作者呼吁民众的诚意。‘我们是战败者,’他们说,‘看看我们这些输了也不生气的人吧,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然而,这些很快被抛到一边,‘我们承认法国人轻浮、冒失、爱吹牛、自私自利,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别的国家,因此?我们的祖国在突然遭遇战争时,一下子变得分崩离析。’这滑稽的公告嘲笑了我们最后的希望。在如此卑劣的行径和粗俗的诡计面前,我们挺直了身子,我们渴望为自己感到自豪。”
俄瑞斯忒斯当然不同意有关苍蝇的故事。但确切地说,那是因为他不是阿耳戈斯人,因为他那“鲁莽的单纯”(朱庇特语)与阿耳戈斯人“有天壤之别,就像有一道深深的鸿沟”把他们分开一样。俄瑞斯忒斯和他的姐姐并非因为怀着同样的理由而反抗。而厄勒克特拉的梦与他的梦交汇在一起,使他从中得到了一种可靠的支撑。它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梦,而是几乎已经上升为一种意愿:“我要我的回忆、我的土地、我在阿耳戈斯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我愿意把这座城市拉在我周围,把自己紧紧卷在里边,就像裹上一层毯子一样。我决不离开这里。”
然而,这个“善良的年轻人”怀有“高尚的灵魂”,他的心里没有仇恨,“从无他求,一直只想行善”。宙斯已“禁止流血”……俄瑞斯忒斯于是恳求宙斯向他表明意志。然而朱庇特’毫不迟疑地回答了他。征兆很明显,俄瑞斯忒斯应该屈膝服从,然后离开……但他没有。这征兆太明显了,朱庇特这么做不可取。俄瑞斯忒斯 那么……这就是善吗?惟命是从,低声下气,“饶命”和“可怜我”总不离口……就这样吗?[略停]善良,他们的善良……
只要再等一会儿,只需片刻的时间,一切都将了结。可是什么都还没发生,但一切已经改变:俄瑞斯忒斯周围的世界被重构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