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说
中古传统的变异与裂解——论中唐思想变化的两条线索
导言
这篇文章要为中唐士人的思想变化提供一一些概括的描述与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对于这段时期的了解能够帮助我们掌握中国思想演变中的一大转向及其原由。学界早已公认,中晚唐到北宋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剧变时期,“唐宋变革”的断案是很难动摇的。在这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得十一世纪的北宋与八世纪的唐代比较起来,在很多方面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诸种变化之中,思想局面的改易是极其明显的一个。八世纪的唐代中国,佛教鼎盛,领时代思潮之风骚,道教与道家意识活跃,社会上洋溢着文学崇拜之风,士人热衷诗文写作,经史之学问津者寡。至于十一世纪的宋代,文学虽仍兴盛,但士大夫以道自任,以政治主体自居,要求回向三代之治,与此一目标有关的学术思想空前发达。在这样的气氛中,又有寻求建立儒家价值之形上与心性基础的“道学”酝酿而出,在思想的领域,佛教和道教已经落居辅助与旁支的地位。用最一般性的历史断代概念来说,这就是中国思想由中古到近世的转变。
唐宋之际的思想巨变不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从韩愈(768—824)的时代到范仲淹(989-1052),大约为两百二十年,到程颐(1033-1107),则有两个半世纪以上。在此期间,思想的变化不是均质进行的,而是有两个明显的突破点。第一个突破点约在唐德宗至宪宗年间(780-820),第二个则为宋仁宗至神宗之际(1023-1085)。这篇文章所要处理的是第一个突破点,这也是本书的首要课题。在开始进行有关中唐思想突破的叙述和讨论之前,要对本文的主题做一些补充性的说明。
首先,前面已经提到,本文试图处理唐宋之际思想变化的第一个突破点,也就是八、九世纪之交的局面。不过,这个突破并非骤然而起,它是一个明显可见的思想变化所导致的。由于这个变化开始于安史之乱前后,本文将以安史乱后的一个世纪左右为主要探讨范围,以求展示中唐思想突破的前因与后果。此外,由于安史之乱后的思想变化触动了中古心灵的基本结构与价值方向,造成中国思想的深层异位,我也必须对中古思想传统的特色有所讨论,以解明中唐新局的历史意义。扼要而言,本文包含了三个层次:中古心灵的特性,安史乱后的思想情态,八、九世纪之交的突破。
如果说,安史乱是个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的事变,安史之乱后思想变化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最简单地说,可以称之为“儒家复兴”。这个儒家复兴潮流的内容,将是本文以及本书所要多方探讨的,文章伊始,我想先提出一个基本的界定,以便读者建立了解的方向。安史之乱后出现的中唐儒家复兴,是一个和缓的旧教复兴。在汉末以后的中古时代,玄学与佛教相继兴盛,再加上道教形成,儒家在思想界的版图遭到压缩,重要性也降低。但是,横亘整个中古时代,儒家依然是一个坚韧不摇的思想与价值系统,孔子仍是人们一致钦仰的圣人,儒经仍为中土圣典,一言以蔽之,儒家在文化中继续占有正统的地位。事实上,在某些领域,例如法律,儒家的力量甚至比以往增强了很多,就社会整体而言,显然是往儒家化加深的方向行进。所以,安史乱后的儒家复兴绝不意味着儒家从荒废的旧墟中重新崛起,这里的“复兴”所指的是,一个多少已经意识形态化的思想传统出现了新活力、新探索,而且有了一些改变——有的还是深刻的改变。这个“复兴”的一个长期后果则是,相对于佛、道,儒家版图大大扩张,造成中国思想结构的改易。
安史之乱后的儒家复兴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基本上是士人群中意识层面的变化,整体而言,相当散漫,尤其在初期,不是个有核心主旨的思潮。这是我以“儒家复兴”——而非“儒学复兴”——来称呼这个变化的原因。不过,在中唐儒家复兴的趋势中,还是出现了两个形迹比较明显的运动。一个是以啖助(724—770)、赵匡、陆淳(即陆质,?—805)等人为首的新春秋学运动,一个是在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古文运动。新春秋学运动是由少数边缘的儒学家所发起,主张从探寻大义的角度来钻研《春秋》,讲究会通经旨,不专主一传,而且,此派学者的经传解释往往掺入了与时势有关的政治理念。在唐代知识界,经学家的角色相当隐晦,新春秋学兴起后,声势也不彰,这个学派是因在八、九世纪之交向文人群传播成功而生出影响的。至于古文运动,一方面是个文章改革运动,其支持者批判近代讲究声律对偶的华美文风,主张文章首当言之有物,文体则可以古为师,质朴有变化,不拘于骈俪;另一方面,这个运动具有更广泛的思想意涵,古文家多主张文章应以经典义理为依归,有些人甚至直接宣扬儒道,乃至从儒家立场进行思想探索。毫无疑问,古文运动是中唐儒家复兴潮流的骨干,这不但是因为儒家复兴的代表人物多为古文家,更重要的是,文人居于唐代文化的核心,地位绝高,文人思想变化所带来的冲击,不是其他群体所可相比的。综合而言,安史乱后的儒家复兴是个广泛的潮流,由于古文运动在其间的核心位置,本文将多涉及古文家,但并不以他们为限。
本文一开始时说,这篇文章要对中唐士人的思想变化进行描述和解释。这是经过斟酌的说法。此一说法意指,我要讨论的只是士人群中的思想变化,这并不能代表中唐全面的思想动态。东晋十六国以后的中古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士人并没有主导时代思想的态势,宗教界——特别是佛教——往往比士人更具思想上的影响力。唐代中叶仍然是如此,在当时,禅宗大盛,诸说并出,震动一时,士人往往对佛教的论说产生兴趣或生出向往,中国思想的域外传播也集中于佛教。就中国知识界而言,安史乱后的儒家复兴只是士人群中的现象,这个趋向什么时候开始对儒佛关系以及整个知识界产生强大的冲击,还有待考索,大概是晚唐以后的事。
在进入本文正题之前,还要说明,本文虽然试图广泛讨论中唐儒家复兴,但并不是一篇面面俱到的通论,我准备根据两条线索来说明安史之乱后的思想情态。这基本上还是一个以解释为重的写法,目的是希望能较清楚地显示中唐思想演变中的关键点以及它们与此前中古传统的关系。安史乱后的思想发展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专门论著的考证辨析才能充分掌握,这篇总说旨在提出一个有整体性的图像,对于本书分论部分或者其他学者已深人研究的问题,一般不再详论,本文的重点将放在既有研究较少或自己新见较多的重要课题。
上篇 文人与文化
要了解中唐思想变化的特色、来由与动力,文人心灵是一条重要的线索。中国自东汉晚期,文学创作兴盛之迹趋于明显,从南朝到北宋,即五世纪到十一世纪,可说是文学的时代,诗文写作的价值高张,文才被认为是才能的首要表征,知识界中的领导者大多为文学家,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世界文化史中也难有其匹。由于文学家自南朝以下长领知识界的风骚,他们对时代文化影响之深,只有佛教僧侣可与比肩,八、九世纪之交的思想突破即是起于这个群体。
所谓文学家,是指擅长诗赋文章写作并以此见知于世的人,本文也称他们为文人。这类人虽然经常来往密切,自成群体,但他们背景多端,形形色色,加上中国中古又有显著的文化、价值多元情况,文学家彼此思想歧异,很难说存在着任何具有确定内涵的文人心灵。不过,文人之间至少有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就是文学写作本身,文人议论文学的结果是,文学思想成为集中反映文人意念的处所——虽然也有些鲜明的文学主张是由非文人所提出。以下,要通过南朝至中唐文学思想中的一个课题来观察安史之乱后思想变迁的面貌及其历史意义。
文人思想中的文学与文化
学者普遍注意到,伴随汉末魏晋以下文风大盛,知识界中明显出现独立的文学观念。所谓独立的文学观,大概包括了两层意识。一层比较弱,指“文”是一种特殊事物,跟其他的人类活动性质不同;另一层比较强,认为有一种“文”异于一般的、功能性的“文”,这种“文”接近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也就是西方概念中的literature,换言之,具有艺术的意味。本文并非文学研究,而是尝试借文学思想中的课题来解明一个思想变局,以下行文将不对中古独立文学观中的两个层次加以区分。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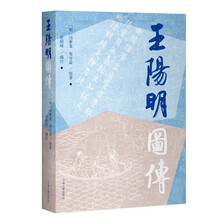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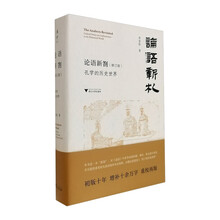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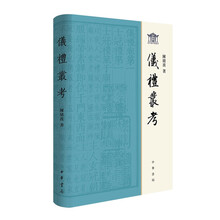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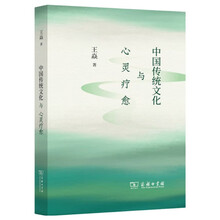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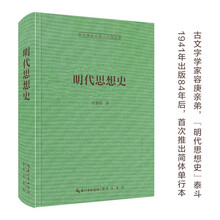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退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 余英时
本书探讨唐代社会的结构变迁、政局变化与某些士人群体中儒学新取向的关系。这是对唐代文士的精神世界与唐宋思想转型过程做出通盘考察的一部力作。对中国学术史,作者研究有夙,因而可以凭借对儒家文化渊源和历代演变的全面了解,梳理隋唐五代不同士人群体的儒学取向、个人之间的大同和分殊,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全书涉及前贤没有关注的许多领域,达到了论学而有宗旨的境界。在考据方面,作者大多在正文,有时也在注脚,缜密核查史事,给予卓有洞见的阐释,展现了作者治学功力。在表述方面,作者尽可能完备地举证史料,纳入周延的论叙架构,纲目清晰、次第谨严。本书拓展读者视野,激发读者就前贤未曾认真探讨的领域做进一步思考。
——台湾中研院院士 张广达
中唐不仅是唐史,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史的转折点。中唐思想史的脉络不仅上涉六朝,而且下连宋明,不仅儒家知识人在危机中思索出路,而日.佛教和道教也在这个充满变异的时代中移形换位。陈弱水教授自从以英文出版了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之后,多年来一直关注着这一时代的思想和文化变迁。在这部新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他思考的范围涵盖了儒、道、佛各种思想,研究的资料也包括了传世文献、石刻资料和佛藏道藏,同时还超越学科的画地为牢,不仅沟通了文学史与思想史,同时也关注到了区域和阶层的话题。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葛兆光
这部著作虽以文化剧烈变迁的中唐作为关注的中心,但实际的讨论涵盖了整个唐代思想变化的大脉络,是作者多年来将思想史的分析和社会史的眼光结合的研究工作的精彩总结。著作中收入的多篇论文相互关联,涉及的都是中国中古晚期文化变化的关键问题和人物。其中既包括了对学界产生诸多影响的经典研究,也有作者最新的思考。作者的讨论真正做到了将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去熟悉化和重新解读,应该说这是过去十年来出版的有关唐代思想文化著作中最有新意和贡献的一部著作。
——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陆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