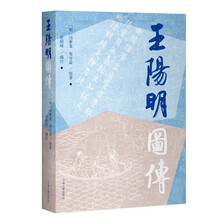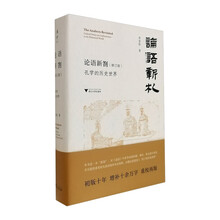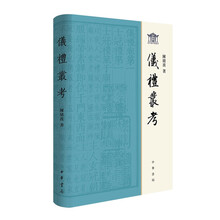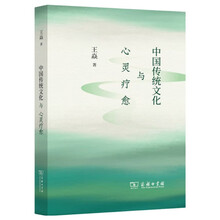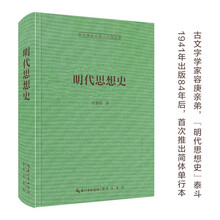“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这同样适用于思想史的研究。注重于“当代”的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研究本身并不是为了针对过去抒发思古之悠情,而是更多地着眼于现在与将来的“问题”意识。如果说思想史研究是一种思想创造的活动,是捕捉古人的思想,重建古代思想的流程,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办法是耍在研究者自己的心灵中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因此,研究者对于古代思想的解读,并不是消极地委身于古人心灵的魅力,而是一项积极的、批判性思维的工作。任何从思想史解读中获得的认识,都涵摄着研究者的思想成分在内。作为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实际上是在活着的心灵与古人的思想“对话”中的一种认识。<br> 一般说来,学术研究有价值的进展都是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开始的。纵观学术思想史,每当历史的进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都有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出现,从而使学术思想的发展线索呈现出阶段性。现在,学术界通常都把中国传统学术分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将魏晋玄学定格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与近代学者章太炎、刘师培最先恢复魏晋玄学的历史地位不无关系。刘师培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待进一步研讨,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撰成于1917年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作为在北京大学讲课时的讲义,虽不是研究魏晋玄学的专著,却是研究魏晋学术思想的精品。对此,甚至对刘师培人品略有微词的鲁迅先生对此书的学术成就也很赞赏。鲁迅在其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评价这本书时说:“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并说:“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而已集》)<br> 中国历史自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末的四百年之间,史家称之为“魏晋南北朝”,此时社会思潮的主流是“玄学”。这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然而,在中国学术界直至20世纪初,魏晋玄学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以致梁启超以“老学时代”概括魏晋学术思潮,误认为魏晋时期“实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当时学者们对魏晋玄学的茫然无知由此可窥见一斑。章太炎的《五朝学》等是较早研究魏晋玄学的论著,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功效,其友刘师培受他的影响,在《国学发微》、《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等论著中对魏晋玄学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对近代魏晋玄学研究也有筚路蓝缕之功。而后鲁迅整理《嵇康集》、汤用彤著《魏晋玄学论稿》、刘大杰著《魂晋思想论》,及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阵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等,都对魏晋玄学研究大有裨益。魏晋玄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在近代蔚为大观,无不受章太炎、刘师培的影响。<br> 具体地说,当代学者对魏晋玄学的研究是逐步深入的。在这里,首先要特别提及的是汤用彤先生的研究成果。汤先生以其深厚的两方哲学素养,将魏晋玄学建构为一种以本末有无之辨为中心的形上学,并确立起一种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他在1938~1947年10年间陆续写成的9篇具有拓荒意义的系列论文,除《言意之辨》外,都发表在当时的《学术季刊》、《哲学评论》、《大公报·文史周刊》等报刊上,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题名《魏晋玄学论稿》。这些论文对魏晋玄学思想渊源、学术方法、哲学特质、发展阶段以及历史影响等诸多学术难点进行了专题研究,构建了魏晋玄学的全面系统的学理体系,尤其是对早期玄学的形成,用力最勤。他认为,汉魏之际的形名学与《易》学天道观的演变,是玄学形成的两大思想来源;“言意之辨”是玄学的新方法;王弼玄学标志着中国哲学从“宇宙构成论”到“本体论”的转变;向秀与郭象《庄子注》的思想特质是以“儒道为一”;道生的“顿悟”说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此外,对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否受到外来佛教影响,以及魏晋玄学的主要发展阶段也提出了独到n尢解。其中,关于玄学的特质是以本体论“体用”方法融合儒道的观点,对20世纪魏晋玄学研究基本思路的影响极大。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