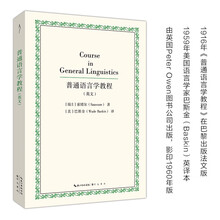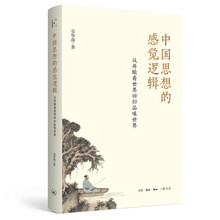在一开始,就标记开始这个时刻,即是书写开始时间性的自身标记。
如何开始铭写时间?如何以个体的方式铭刻时间——铭写“我的时间”?个体的书写是何时出现的?这在文明的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谜,它关涉何为个体性的问题,以及个体与写作的关系,关涉写什么、如何写(所谓的显白与隐晦书写的差异)的问题;进一步,则是“写”与“不写”的问题——即书写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问题,个体之不可能性的书写指向生与死之问的时间性差池、死后生命的余存,以及未来之先行的时间性疑难,个体性的形成与书写的时间性有着内在的联系。
所谓各个文化在轴心时代的开创者,比如苏格拉底、孔子、耶稣等等似乎都是述而不作的这个现象(但犹太教的摩西却是例外),其实隐含着一个时代转变与灾变的症候,如同摩西五经的书写乃是犹太人出埃及的申命之记录,出埃及的过程都是摩西与法老之间以灾变形式呈现的斗法,这即是对灾变之持续的书写。就希腊文化而言,除了悲剧表现个体生命突转的灾变经验,柏拉图围绕饮毒鸩而死的苏格拉底这个哲人展开的哀悼书写——已经是不可能的书写,也当然已经是灾变书写,而且也是余存书写,试图让苏格拉底再次在戏剧式对话中以灵魂不死的形象活过来。中国文化的绝地天通、大禹治水,以及殷商甲骨上大量对灾异的记录,文王的演《易》等等,尤其是中国人对吉凶祸福之最为独特的生命经验,似乎对灾变的普遍性尤为敏感。中国思想的独特性就在于以灾变的情态打开了基本的实际性生命经验的场域,并且与原发的生与死,有限与无限的经验相关。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