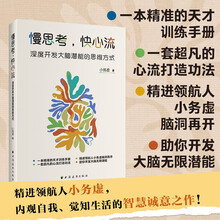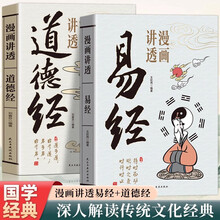儒学总论<br> 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br> 汤一介<br> (北京大学哲学系)<br> 我写过一篇《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在该文中提出一个想法:当前我国文化在西方哲学冲击之下,似乎很像我国文化在南北朝受到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之后的隋唐时期,即由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阶段转向本土文化开始消化外来文化的阶段。我们知道,印度佛教文化至隋唐,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华严、禅宗等。我们之所以说这些佛教是中国化的佛教是因为他们吸收了中国文化的某些思想,而对印度佛教文化有所发展。所以我常说,中国文化受惠于印度文化,而印度佛教文化又在中国得到了发扬光大。我们可以看到,天台、华严、禅宗在心性问题上融合了儒家的心性学说,天台甚至吸收着某些道教思想,而华严、禅宗无论在内容和方法上都与老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说,那时在我国正在经历着使中国本土文化加入到外来文化之中,使外来文化更加适应中国社会生活,从而使外来文化中国化。对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可以用冯友兰先生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来说明。至隋唐,我们对印度佛教文化已经走出了“照着讲”的阶段,而正在转向“接着讲”的阶段。我想,如果今天我们要想使中国文化得到发展,而且在当今人类社会中发生重大影响,那么我们就应该走出对外来文化的“照着讲”的阶段,下面将以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为例,谈一些我的看法。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可能有多个“接着讲”的方向,我想至少有三个重要的“接着讲”的路径:一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二是接着西方某种哲学讲;三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br> 一、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br>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中国哲学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大量吸收着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渐使中国哲学实现向现代转型。我们可以说,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界已经在创建现代型的中国哲学上作出了可观的成就,先有熊十力、张东荪,后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等。他们的哲学不只是“照着讲”中国传统哲学,而且是“接着讲”中国传统哲学。为什么说他们是“接着讲”中国哲学,主要是他们能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来讨论和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哲学的“照着讲”和“接着讲”问题是冯友兰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新理学》不是照着宋明理学讲,而是接着宋明理学讲。他的“接着讲”实际上是把柏拉图的“共相”与“殊相”和“新实在论”的思想(如“潜存”的观念)引入中国哲学,把世界分成“真际”(或称之为“理”,或称之为“太极”)与“实际”,实际的事物依照所以然之理而成为某事物。冯友兰哲学把世界区分为“真际”与“实际”,一方面上可接宋明理学“理一分殊”的学说,另一方面又可以把西方哲学有关“共相”与“殊相”的思想(如柏拉图那样)贯穿于中国哲学之中。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之所以“新”(如冯先生自己所说是“旧瓶装新酒”)就在于他用西方哲学的某些思想来分析中国哲学问题。冯友兰为了应对维也纳学派洪谦对他的“新理学”形而上学的批评,他写了一本《新知言》从方法论上说明他的空灵的“形而上学”和旧形而上学的不同,并企图从方法论上调和中西哲学。他认为,西方哲学长于分析(形而上的正的方法),中国哲学则长于直觉(形而上的负的方法),他用以建立“新理学”形而上体系的方法是两种方法的结合。这就是说,“新理学”不仅是接着中国哲学讲,而且也是接着西方哲学讲。这里我们不是要讨论冯友兰的说法是否对,而是要说明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某些哲学家尝试着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使中国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以便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br> 如果说冯友兰先生是“新理学”的代表,那么贺麟先生也可以说是“新心学”的代表。贺先生有一篇著名的文章《知行合一新论》是讨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的,它之所以是“新论”,就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一样是“旧瓶装新酒”。《新论》首先利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分析了“知”、“行”两个概念,并说:“‘知,是意识活动,‘行’是生理活动,所谓‘知行合一’就是这两种活动同时产生或同时发动。”贺先生把这种“知行合一”称为“自然的知行合一论”。这个“知”与“行”同时产生或同时发动虽是源自西方哲学家斯宾诺莎,而贺先生进一步给以解释说:“知行合一乃指与行为同一生理心理活动的两面而言。知与行既是一活动的两面,当然两者是合一的。”这可以说是利用近代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知识而得出的结论。贺先生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一种“价值的知行合一观”,自有其德行和涵养心性方面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的知行合一观”应有知识论的基础,因此贺先生说:“不批评地研究知行问题,而直谈道德,所得必为武断伦理学。”而他的“自然的知行合一论”可以包含王阳明的“价值知行合一论”,又为其提供了合理的知识基础。贺麟先生的这个《新论》虽然有其可以讨论之处,但它确实是一“新论”,其“新”就在于引入了西方哲学和近现代科学知识,并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若干问题。据此,《新论》不是“照着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而是“接着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br> 如果说冯友兰、贺麟都是在欧美直接受过系统的西方哲学教育,那么熊十力则没有这样的机会,他的西方哲学知识大都是阅读翻译的西方哲学著作或听了张东荪对西方哲学的介绍,但他无疑也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现代型的中国哲学家,而且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他的《新唯识论》和《体用论》都是讨论“本体论”问题的。他认为,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意谓离用无体,不可于用外求体,这无疑是讨论“本体”与“现象”的问题。并据此以批评西方哲学把“本体”(实体)与现象分为两重世界,他说:“西哲以现象是变异,本体是真实,其失与佛法等。”(按:熊十力认为,佛教以“不生不灭、无为,是一重世界;生灭、有为,是另一重世界。”)关于“本体”与“现象”的问题,可以说自古希腊哲学以来就是西方哲学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我不讨论熊十力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是否完全正确,但他确实是对西方哲学有所了解。不仅如此,而且熊十力在讨论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上,就其主张宇宙大生命而言,受叔本华、柏格森的影响是很明显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体系只出版了《境论》部分,即“本体论”部分。本来还要写“量论”部分,即讨论有关“认识论”epistemology的问题,虽然“量论”没有写成,但在他的《原儒》等书中,我们大体上可以了解他所要建构的“认识论”的基本框架。熊十力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比较重视体认(心的体会认知),而不注重“思辨”的分析,因此“中西文化,宜互相融合”,“中国诚宜融摄西洋而自广。”他主张把中国的“体认”与西洋的“思辨”结合起来成为“思修交尽之学”。这正表现了当时中国学术界一种共同的看法,认为需要引进西学近代的“认识论”以充实中国原有对“认识论”上的不足。<br> 冯友兰、贺麟、熊十力对中国传统哲学不是“照着讲”,而是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努力吸收西方某些哲学思想,“接着讲”中国哲学,以建立现代型的中国哲学。 <br> 关于金岳霖先生的哲学是接着中国哲学讲,还是接着或照着西方哲学讲,在中国哲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冯友兰在他的《三松堂自序》中说:他自己的哲学是“旧瓶装新酒”,而金岳霖的哲学是“新瓶装新酒。”那是不是说,金岳霖的哲学与冯友兰的哲学有相当大的不同呢?最近看到俞宣孟教授的《移花接木难成话——评金岳霖的(论道>》,他认为《论道》的观念和方法都是西方的,《论道》企图解决的问题是西方哲学的问题,他说:“金岳霖《论道》这本书完全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观念来写的。所谓‘元学’,其要旨在于建立一个纯粹理论的世界。既为纯粹理论的世界,又要兼顾现实世界,这是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一向存在的二元困难。金岳霖在《论道》的绪论中试图解除这个困境,但是结果表明,他自己也陷入了这个困境中。”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金岳霖的哲学是接着中国哲学讲呢,还是接着西方哲学讲呢?胡军教授的《道与真——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有种分析,他认为虽然金岳霖的“很多哲学问题都是直接从批判休谟哲学出发,如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就主要是用来解决休谟的因果问题或归纳问题。”并说:“金岳霖是在继承罗素、刘易斯等人的有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先验性的理论,并以先天性命题和先验性命题这两类命题来建构其形而上学的体系。”但是我们是否就能说金岳霖先生建构他的哲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西方哲学的问题呢?在《道与真》中说,金岳霖先生写《论道》是因为“他竭力要把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道内化自己的思想与生命之中。”因为照金岳霖自己说:他“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于不知不觉中,也许得到了一点学中国思想底意味与顺于此意味的情感。”“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之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对于这样的道,我在哲学底立场上,用我多少年所用的方法去研究它,我不见得能懂,也不见得能说得清楚,但在人事底立场上,我不能独立于我自己,情感上难免以役于这样的道不安,我底思想也难免以达到这样的道为得。”这就是说,金岳霖虽然把许多西方哲学讨论的哲学问题引入到他的哲学体系中来讨论,但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哲学的问题,丰富中国哲学的内容,以便使中国哲学能走向世界。就哲学问题说,金岳霖其实讨论最多的也还是当时中西哲学都十分关注的“共相”与“殊相”的问题。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说:“在30、40年代,关于共相的讨论是中国哲学界都感到有兴趣的问题,特别是共相存在的问题。……共相不是殊相,不在时间空间中占有一定位置,它超越特殊的时空。就这一方面说,它是Transcendent。但共相不能完全脱离殊相,如果完全脱离,那就只是一个可能,而不是现实的了。就这方面说,共相又是Immanent,这种情况就是所谓‘一般寓于特殊之中’。经过这样的分析,不但当时争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理学中关于‘理在事上’、‘理在事中,的争论也成为多余的了。”因此,冯友兰说:“新理学的一个代表人物是金岳霖”。金岳霖的哲学虽然讨论了许多西方哲学问题,从形式上看颇似西方哲学,但他的目的和感情仍然是为了解决中国哲学的问题,使中国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也许是中国现代哲学必经之路。我们今天再讲“中国哲学”,应该特别注意接着金岳霖的路子来讲。<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