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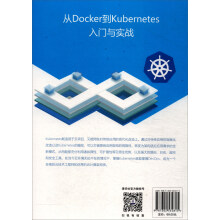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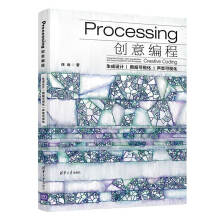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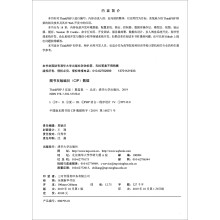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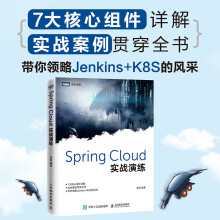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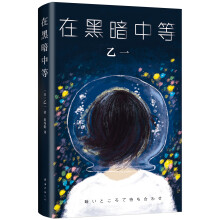





他的看法是:“如果将这些记载直接看作史实或许没有什么价值,但却可以为《史记·商君列传》从一个角度记载的军功性财物臣妾归属制的存在提供参考资料”,同时它们还提供了一些线索,使后人能据以推测按军功行赏的数量基准。
随后,平中苓次又深入研究了《荀子》“五甲首而隶五家”的含义,认为这意味着“将五家已耕作、已居住的土地,作为附属于爵位的禄(采地)进行赏赐。因此,有爵者得到了这些土地,就像取得了自己的私有地,并使耕种这些土地的五家作为自己的隶农,如同臣妾那样归属自己,进而向耕种者收取地租。可以这样试想,身份性土地归属制本身并不是新的制度,而是在卿、大夫、士这些诸侯的家臣中已经实施的制度。……既然如此,商鞅变法之所以要发动的理由何在?必须看到,变法并不是针对原有的卿、大夫、士等特定身份阶层,而在于它适用于一般庶民”,由此可见爵制性大土地保有制的特色。
在该文的末尾,平中苓次总结道:“这一爵制性大土地保有制的开创,促进了在民众之间私有地主的产生。”这说明,他认识到秦代的爵制性大土地保有制与汉代以后大土地私有兼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
笔者看到这个鲜明的论点,极受启发,但读过几遍之后,则不禁产生了以下疑问。
第一,秦代的爵制性大土地保有,与汉代的大土地兼并,是否真有一系列关系?根据平中先生的论点,有爵者受赐的田宅,就像爵位附带的采地(禄)一样。如果真是这样,有爵者就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营田宅,而只享有从在田宅里劳动的隶农那里收取地租的权力。地租率虽不明确,但若是按孟子等人所说,也许就是所谓的“什一税”。但与此相反,如文献所记载,汉代大土地所有者兼并田宅,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当然,在广大的土地上通常是奴隶和佃户劳作,但就佃户而言,地主要向他们收取收获物的一半,有时还会超过一半。
……
守屋美都雄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对中国古代岁时记的研究,这也是对与家族问题相关的民众节庆活动的探索,是一项以文献学为主要内容的扎实细致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岁时记研究将有可能被再往前推进一步。
——(日)山田信夫布目朝讽山本宪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