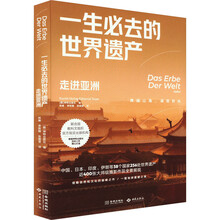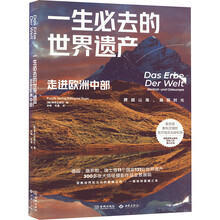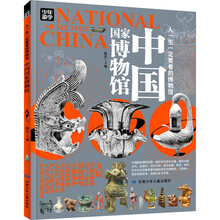么羡慕住在一院的孩子,家属楼的边上就是食堂,每天都能闻到那饭菜的香味就是最大的福气了。对我而言,每次去一院都像是过节。看电影《奇袭》,到游泳池去泡水,看一场隔壁梅林罐头厂罗马尼亚实习生与学校教师的足球比赛,甚至与那些割草贴补家用的校工孩子一起去一院的操场割草,也是我最喜欢的娱乐。
这都是在1972年以前。学校南迁之后,只在校园里留下几间屋子作为水产学院的留守处,我常去那里领取父亲每月留给我们母女的部分工资。别的建筑都被什么陶瓷仓库、教育学院、招待所等瓜分一空。
大门虽还能随便进出,但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是必须面对的。本是同根生的东海水产研究所念在手足情分上,尚允许水院的家属去他们的浴室洗澡,但他们的家属只收五分钱,水院的家属要收一毛钱。一回我和邻居结伴去洗澡,我的票子尚未用完,便在屋外等着。邻居是东海所的家属,就买五分票。售票的是我一个同学的母亲,她看到了窗外的我,以为我图便宜让人代买冼澡票,再三盘问买票的女孩是不是买了自己洗。在寒风中等了很久的我知道原委后,屈辱的感觉任浴室的大龙头怎么冲洗也挥之不去。直至今天,当我每天在家舒服地洗澡时都时常会泛上一种酸楚的感觉。
留守处,是个特殊的名词,是上海的家属与厦门的亲人之间的一个联络站,有点像厦门水产学院驻上海“大使馆”。我去领父亲的工资时,顺便打听一下最近有谁回厦门,欲给父亲带些卷面猪油一类的食品。那个晚上,我陪着母亲到留守处给父亲打长途电话,为商量换房的事。学校给了我家两间房,但因楼层和邻居的原因,让我母亲犹豫难决,留守处便让我们同父亲在电话中尽快商定。这是我和母亲第一次打长途电话,很难打通。好不容易接通了,又说父亲不在宿舍。那天集美小镇正放电影,那头的热心人便到电影院让人举牌寻找。第二天,几乎所有碰到我父亲的同事都关心他家发生什么大事了。那年代,打长途是有些惊心动魄的。每到寒假,我和母亲、妹妹一同去留守处坐上安排好的客车到北站接父亲。留守处的存在,犹如寒屋中一个废弃的壁炉,虽已无甚光热,但经常望见它,还能给人一丝慰藉。
鹊巢鸠占的日子里,教育学院始终都是水院人心目中的入侵者,而到了水院人急欲归去来兮的历史性时刻,它更成了最大的障碍。奇怪的是,把它赶走另给它找个新校址竟成了水院普通教师的义务。我的父亲和一帮同事去各有关部门呼吁“还我老家”,他们甚至找了教育界名人谈家祯。最后,也不知是哪个环节起了作用,“眼中钉”终于拔去。1980年初夏,我与我的儿时好友思梅在一院一间刚腾出来的宿舍里重逢。思梅他们几个男孩女孩是经过特许提前回沪入籍参加高考的,他们的父母户口和人都还在厦门呢。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