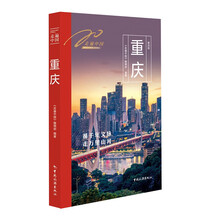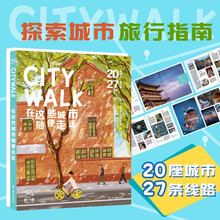香江之恋
1989年8月,我初次踏入香港——当时还罩着神秘面纱的这座东方大都市。在罗湖口岸,跟随着长长的人流缓慢行进中,我心里千百次地问:香港、香港,你是怎样的一座城市?
初临香港
最先认识的香港,是维多利亚港,这是香港的灵魂,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香江”——在香港地图上,你找不到“香江”这条江,但是,你绝对会相信,也自然会接受,维港就是“香江”。
我当时住在湾仔海旁的湾景中心大厦,那是华润集团员工的宿舍。先生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这个当时号称内地在海外最大的外贸机构工作。湾景中心紧靠维港最美的一段。我每天早晚都要到维港海边与大海约会:看着天星小轮忙碌往返,听着柔和的涛声,整个人都沉醉了。自那时起,我懂得了“梦幻”这个词汇的意义。
之后,我去了香港的大大小小海滩,触摸着各处那千万年不停涨落的海水。每个海滩,每个海域我都发现了它的独特处:有的水清沙细,有的碧水黑沙,还有的五彩海水;有的地方清幽如世外桃源,有的地方一水平镜有如圣湖……
香港还有不少当时令我称奇的地方:上午时分路过位于湾仔近演艺学院的路,路旁虽有精致的小公园,有如苏州园林,但行路疲乏的我却不敢在此小憩,只是因为太缺乏人气:除了些许汽车外,不见一个人影——这可是寸土寸金的香港哦,当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000多人,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
中环有如魔法城,正午,中环大街小巷万头攒动,满眼望去,到处是着西装的男士和穿套裙的女士,拂面而来的都是“活力”。而晚上,这里不仅人流稀少,而且灯火暗淡,店门早闭,寂静得犹如一座睡城;
这里的人很西方(英国),也很东方(中国):无论是进酒店进电梯,还是走在狭窄的路口,男士总是很自觉地侧身让路;与你分手时,稍稍一弯腰,一副英国绅士的派头;而不少酒店,门前有水车,大堂有财神。有时,路过一些店铺,还能看见烧符烧纸钱;
但是,对于香港这块当时还没有回归的土地,我完全是一个外来者。多少次,我向当地人问路、我进入高档皮草店看服装(那时,皮草专卖店不是大门敞开随便进入的,必须先按门铃,店主看你像购买者,才会给你开门——也许是害怕抢劫吧),都有人热情相助,但最后不忘问我一句:“日本人?”“不是。”“台湾人?”“不是,我是内地来的。”对方狐疑,摇头:“不像。”然后,撇下我。那时的香港人,因为创造了经济奇迹而骄傲,因所谓“九七大限”而担忧。
那时内地人在香港是受歧视的。当时香港正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楼市股市兴旺,而内地刚开始改革开放。由于不少港人在内地有穷亲戚和乡邻,内地大门刚打开,就有不少穷亲戚包括一些基层干部涌来香港这个想象中的“花花世界”,甚至向腰包鼓起的港亲港戚“化缘”。于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表叔”便成为港人对内地人的统一贬称。据说,那时,走在街头就能分辨出谁是“表叔”。先生告诫我,出门一定得带上护照(当时还没有通行证),皇家警察查得紧。好在香港是个注重形象、讲究衣装的地方,虽然我的一口普通话在“莺歌鸟语”中常常暴露“身份”,但一个月下来,没有一个人为难我。
即使是这样,我也有一种耻辱感。好在我当时只是这个社会的旁观者。不过,也正是这样,更勾起我对香港社会的好奇:仅仅靠一条深圳河,就能将两边的人划出两个等级,甚至仅仅借助衣着,就把我与深圳河以北的人们划分开来,这是一种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
香港,我要认识你,我要深入认识你。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