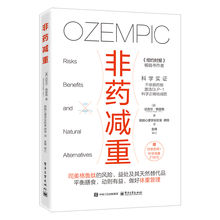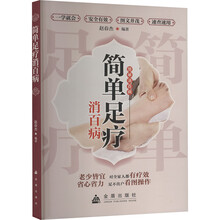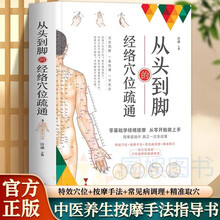第一章 健康是我们共同制造的幻想
班达海上风雨飘摇中的登陆艇
“咂啷——”、“咂嘣——”
“救命!”
满载的海军登陆艇仍旧像树叶一样摇荡着。这条一个世纪前制造的旧船似乎马上就要被汹涌的波涛吞没了。
1972年7月,我在印尼东部的班达海上,暴风雨正在逐渐减弱,此时虽是白昼,但海面上有些昏暗。
这时,船上的一名印尼年轻人坠落海中。
船只已迷失了方向,谁都不知道前方究竟是新几内亚还是苏拉威西,亦或巴厘岛。为了将落水的年轻人从海里救起,船长急忙调转了船头。
年轻人终于得救,我舒了一口气。这时,刚刚死一样沉寂的船上,人们忽然跳起来叫喊:“布鲁岛!布鲁岛!”
原来几个眼力敏锐的印尼人已经辨认出远方依稀的岛影。
我也凝神远望,却什么都看不见。在云层的缝隙中,只有灰色汹涌、一望无际的班达海。
我已经虚弱得几乎无力站起。因为晕船晕得厉害而不停呕吐,早在两天前胃里的东西就被吐光了。
上船前准备的“饭团子”早已吃完,印尼人分给我的香蕉也所剩无几
可对于我来说,比食物更严重的问题是经受了三天三夜的雨淋,身体已经彻底冰冷。我只觉得寒气阵阵,浑身不停颤抖。
出发前我租用的登陆艇上现在挤满了印尼人,几乎没有躺下的空间。
他们身上有一股特殊的体味,年轻姑娘头发上搽的椰油散发的气味也让我厌恶。大家都是从安汶岛前往布鲁岛的。当船只卷火凶猛的暴风雨中时,两个女孩子就从左右抱住我,叫道:
“papa(叔叔),papa(叔叔)!”
“sava,maty(我要死了)!”
年轻女性富有弹性的肉体从左右靠紧我,她们身上散发着令人头晕的体味和椰油的气味。我既兴奋,又感到有些害羞和张皇失措。不一会儿我又因为船的剧烈摇晃而呕吐了。
由于我浑身发冷,这时不管是不是年轻女孩,都希望他们能贴紧我。我只想要他们身上的温度,我的牙齿不停地打架。此时能让我止住颤抖的只有他们的体温,即使有体味也无所谓了。
文明的偏见
当时我还很年轻,在东京大学传染病研究所研究热带疾病。一天,主任教授命令我说:“在印尼的伐木场有日本人病死,有的患上重病,你去调查一下原因!”
我原本是个懒惰的人,只想在奄美或冲绳等南部岛屿过悠闲的生活,由于自己并不自信能成为城市里的医生,所以只想“做南方岛屿上无医村的医生”。就是抱着这种轻松的心情,我考取了传染病研究所的研究生,开始了学习生涯。
佐佐木教授简单地说了一句:“没什么大不了的,印尼的调查你只需一个月就足够了。”
此时从日本出发已有两个月。我在最初的调查地加里曼丹岛患上了伤寒,因此白白耽误了两个星期,自己打针才勉强痊愈。
第二个调查地是布鲁岛。这是班达海域比较大的岛屿,以前曾经是流放犯人的地方,这里不用说飞机,就连定期的航船也没有。之所以到这里是因为日本商社对布鲁岛上的柳安木材感兴趣,所以派遣了几名日本人去岛上指导和监督采伐木材。其中一人死于原因不明的热带病,另一人已经持续发热一个月以上。
为抵达布鲁岛,我先乘飞机从加里曼丹岛的马辰市飞往距布鲁岛最近的城市安汶岛安汶市,听说从那里租船两天就可以到达布鲁岛。
我很快在安汶岛找到了船,是一艘海军登陆艇。登陆艇表面看很结实,船长也表示多次去过布鲁岛,我便毫不犹豫地决定租用此船。
可是出发当天我去乘船时,意想不到的是船上已经挤满了印尼人,根本没有我的座位。
我马上跟船长抗议道:“这是我包租的船,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乘坐?”
船长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些人都要去布鲁岛,为了这个机会大家等了很久,有人甚至等了两个月,所以船满员了。”
“船长你实在荒谬!这船是我包下来的,我出钱包下了整艘船,没有我的许可,他们怎么可以上船?”
“是你这位日本的博士太荒谬了。这船是开往布鲁岛,大家都有事要去布鲁岛。我没说不让你上船。别说傻话了,博士!”
我想反驳,却一时无语;怒不可遏,又不知该说什么。
我询问了其他人才知道,船长向船上的每一名印尼人也都收取了船费。再向船长核实,他竟然满不在乎地回答:
“当然了!哪有不给钱就上船的?大家都是看情形收费,这是常识。”
“那好,他们给你多少钱,我全额支付,让他们下船!”我再一次逼迫船长。
船长不停地摇头,无奈地盯着我:“我不是说过了吗?这些人都要去布鲁岛。博士,你是听不懂还是太小气?少哕唆,快上船!”
我的脑子越来越乱,一时失去理智。突然我想起自己是柔道二段,正想朝船长胸前抓去,这时我的随从,一位日本商社的年轻职员说道:
“先生,在印尼就按照印尼的规矩办吧。”
他虽然是在劝慰我,但这话的语气就好像是我做错了。
于是,船长载着仍然不停发牢骚的我和众多印尼人,一路驶向布鲁岛。天气说变就变,不久前还是繁星满天,突然下起雨来,片刻间狂风呼啸、暴雨袭来。陈旧的海军登陆艇在暴风雨中像树叶一样飘摇着。
我以为船上至少应该装有罗盘,可船长竟然说:
“那玩意从来就没有。只要有星星就可以准确开往布鲁岛,可现在没法知道方向。”
听了这话,我感觉只有听天由命了。没有“感谢"一词的社会
幸运的是“远方依稀的岛影”正是我们的目的地——布鲁岛。七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抵达布鲁岛。船上的印尼人扛着大包小包欢呼着下了船。抱着我的两个年轻姑娘也不知何时没了踪影。
“实在是倒霉透了。”
我完全消瘦了,眼睛也凹陷下去。同行的日本商社职员也没了精神。他叫齐藤修,毕业于日本某大学印尼语专业,其后又在印尼大学留学,是一个“印尼通”。
“遇风暴时我一时不知怎么办好,如果让博士死在这,东京本部的部长不知会怎么说我……啊,幸好没出事。”
“真想不到会遇上风暴,最让我无法容忍的是我包租的船,船长和船上的人竟然个个理直气壮。”
我对这件事还在耿耿于怀。
“而且竟然没有一个人说一句感谢的话……”我这样嘟嚷道。
年轻的齐藤稍稍退后一些,说道:
“印尼语的‘谢谢’叫‘terimakasi’。意思是“我不客气了”也就是说,有钱人和生活阔绰的人,在各方面向其他人‘布施,是理所应当的。”
他似乎认为我这样计较,不停地表白自己的合理性是明显错误的。我意识到再说下去只会让人反感,虽然还是耿耿于怀,但决定不再提了。
谁知两天后,那个船长居然来找我说:“我载你回安汶岛,价钱给你优惠。”
我声嘶力竭地把他轰走了。而我们也因此不得不等到日本的木材船来布鲁岛的时候再离开,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两个星期……
布鲁岛上有八名日本人,他们在由印尼公司和日本商社合资成立的木材采伐公司工作。公司不仅在山里采伐柳安,还铺设了公路,搭建了桥梁。有了这些公路和桥梁,以前居民需要三天才能到达的街市,现在一天就可以到达。特别是有人突然生病时,公路和桥梁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在布鲁岛有两三个安装了电灯的部落。由于成立了公司,形成了劳务市场,所以突然从安汶岛来了很多人。
在去往热带雨林山中的采伐现场的中途,日本人建立了木材采伐基地,那里有发电设备,有参与采伐和公路建设的印尼人住宅。日本的工作人员也在那里建造了住所。
虽说是“住所”,其实只是能睡觉的简陋工棚。晚上9点停电,电视就更不用说了。最让我吃惊的是,那些日本人的住所竟然没有厕所和浴室。
这里是潮湿地带,粪尿很难渗入土地。他们也和当地人一样,没有搭设厕所和浴室。
或许是公司出于高度的政治“觉悟”,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印尼人,对所有劳动者都一视同仁。
于是我们选了其中的一间作为我们的宿舍。
边跑边解手
有一条小河流经基地中央。不,应该说公司以河流为中心建造了基地部落。浑浊的暗红色河水悠悠流淌,河两岸稀稀落落地立着一些小棚子,这就是厕所。
小棚子的上游有用木板拼成的“围墙”,那是浴室。虽说浴室处于上游,但紧挨着浴室的还有厕所。也就是说,人们是甩和粪便一起流淌下来的河水“洗澡”的。
日本人的住房比较靠近河流的上游。但在上游,一些和公司无关的居民随意在河两岸搭建了房子,当然也有厕所。
很多居民将河水当做饮用水,洗衣用水也是河水。另外,在岛上没有公路的时候,这条河曾是一条很好的“通路”。它是去街市最近的路,当地人熟练地驾乘简陋的独木船,外出到很远的地方去。
我首先对用这条河的河水洗澡产生了抵触情绪。
当时,我刚刚在传染病研究所开始针对病原微生物进行感染症的研究,我当然清楚冲洗粪便的水中含有多少病原微生物。我认为这样“洗澡”很有问题。可是在高温湿热的布鲁岛,如果不每天洗澡,人就皮肤发黏、无法入睡。
傍晚,当工作结束后,洗一个澡最令人神清气爽。仅仅过了三天,我已经能很自然地用河水洗澡了。
接下来的麻烦是去厕所解手,谁知道天黑以后这个岛上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布鲁岛,有的蛇比人的身体还大。我偶然在采伐场见到了实地工作人员捉住的大蛇,有我身高的两倍长。天黑后,我去河上的厕所时,当地人吓唬我说:“大蛇会爬出来,狠咬博士的要害处!”
因此厕所必须白天去。可厕所有很多缝隙,而且根本没有门,白天解手会被别人看见裸露的身体。事实上,我们住进宿舍的当天,附近的孩子们就好奇地聚过来看,怎么也不肯离去。
因为之前的航行,我在船上没有解手,忍不住跑进河上的厕所。刚一进去就听见大笑声,厕所前面已经排了一队人墙,让我最终都没能“释放”出来。
再次感到便意,我悄悄地从房间溜出来,跑到附近的灌木丛,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蹲下来。这下坏了,臭味马上引来了很多昆虫:苍蝇、蚊子、蠓虫,最后包括牛虻都飞来,一起进攻我的屁股。我觉得疼痛,但同时感到排泄的轻松。我忍受着昆虫的前后夹击,继续解手。突然后面的灌木沙沙作响,回头一看,两头野猪正朝这边跑来。
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狼狈,内裤也来不及提,叫着“救命”,一溜烟地跑回宿舍。
后来才知道,野猪是周围居民放养的,并且居民们还确切地知道哪一头野猪是谁养的。
“博士,不是和你说过嘛,厕所建在河上是有原因的。”当地工作的日本人这样告诉我说。
这时我想起了一篇纪事,记述演员渥美清在非洲大草原苦于没有厕所,在树荫下解手,结果遭到苍蝇、牛虻的袭击,他一边跑跳着一边解完了大便。
“排除积便"的文化人类学
“还有,河上的厕所也不安全。经常有黑寡妇蜘蛛在厕所的角落里拉网。它会咬你的要害部位,一旦被咬,那里就肿得厉害。还有……”
“什么?还有?”
“是啊,河里有很多鱼,都在等着呢。”
“什么?在等什么?”
“博士的排泄物啊。日本人的排泄物好像特别受欢迎,引来的鱼比印尼人的多。”
以前,日本也有“收粪便”的生意,根据卖出人的地位职业,划分粪便等级。《粪袋》(藤田雅矢著新潮社出版)一书记载着这样的事情:在京都,鸭川流经的“先斗丁”附近一带聚集了一些粪便商,并组成了名为“粪座”的行会。行会中有专门鉴定粪便的肥料评价组,由他们来决定一桶粪便的价格。
粪便鉴定员取少量粪便,先闻气味,再看里面,逐个定价。肥料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甲和乙是烟花巷和官府们的;京极一带最多不过是丁级;水分多、难以运输的被划在“等外”,卖不上价钱。也就是说,“粪便”是有差别的。
“鱼也分得清粪便的好坏。”
“那和我去厕所有什么关系?”
“所以,解手的时候要抬抬屁股,抬得晚了会被鱼咬到……”
不管这话是真是假,我在河上厕所解手的时候,的确听到下面河里的鱼会突然骚动起来。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河里的鱼一定为了迅速捕捉猎物而纷纷跃起了。
在旭川市开设肛肠科诊所的国本政雄先生,曾经就“厕所与排便”这个项目进行过有趣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市内304名小学生。结果发现,3/4的小学生有憋便行为,六成以上的学生不使用学校的厕所。他们说:“学校的厕所又脏又臭,加上自己难为情,所以不在学校厕所大便。”
根据调查结果,回答便秘或有便秘倾向的学生占12.9%,“经常憋便”或“时常憋便”的占76.7%,不在学校大便的学生占到了63.4%。
以多种回答方式调查不在学校排便的理由中,回答“脏”、“臭”、“心里别扭”、“难为情”的占12%~20%,此外还有“被嘲笑”、“被欺负”之类的回答。
国本先生又对办公室女性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很多人“高中以前就开始便秘”。国本先生分析说:“便秘的主要原因是抑制便意,而小学生们常常勉强憋便。”
这和我们在布鲁岛上“便秘”的原因完全不同。但我对于日本小学生六成以上“抑制便意”的调查结果感到非常吃惊。
收集“粪便”
即便这样,我的“便秘”总是无法消除。在河边宿舍住了一个多星期后,我和当地的孩子们成了好朋友,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我从没见过孩子们去河边的厕所,所以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去厕所?”
“大家早上起来就下河了。先洗澡,然后把腰部以下泡在河水里解手。”
“那么那个小棚子谁用?”
“爷爷奶奶,还有病人和不会在河里解手的小孩。”
“是吗,难怪谁也不去厕所。”
“博士,你在那小棚子能痛快地解大便吗?我们在那里都解不下来。”
“在河水里好受吗?”
“嗯,屁屁也干净……”
“可是不会被鱼咬吗……”
“有时会有鱼犯傻赶过来,那就捉住它。早饭时用它做菜,味道很香呢。”
什么都需要尝试,我马上进入河里,可是怎么也不行。
在布鲁岛停留的时间比原计划延长了,我决定以这些孩子为对象做一些调查。我想收集孩子们的粪便,检查他们患什么寄生虫病。
可我马上意识到这非常困难。他们都在河里排便,不在陆地上。
可既然决定要做,我也不想轻易放弃。为收集孩子们的粪便,我考虑了一个计策。从日本出发时,我认为也许用得上,带了很多气球。我把红色的绿色的气球吹起来,对孩子们炫耀说:
“谁把自己的‘便便’拿来,就给他这个。”
可一天两天过去了,没有一个孩子拿“便便”来。倒是有两个孩子确实拿来了,但仔细一闻,是狗屎。
“为什么不拿自己的‘便便’?”
“因为妈妈说不可以在地上解手。”
“为什么?”
“会被蛇和熊咬,还会被蚊子和牛虻叮……很早以前就有不许在地上解手的‘规矩’。”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