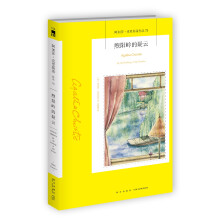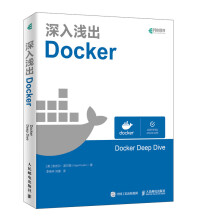第一章 帝国的创建:应运而生
葬礼,家族的阴影
回顾起来,安杰利的家族史看起来俨然一部胜利者的史诗。但胜利铸就的王冠虽然辉煌,却往往过于沉重,以至这个家族中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承受这样的荣誉、财富和与之相应的压力——这种不堪重负往往导致悲惨的后果,因为生命与死亡仅仅只有咫尺之隔。
与世界其他大家族一样,安杰利家族既充满了耀眼的光环,也饱尝过各种悲苦,家族中的懦弱者无法承受上代胜利者过分的重荷而选择了自我了结——这个家族中并非人人都是英雄豪杰,他们中的大多数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在这样的家族王国里,也许生来就已经拥有了一切,可这反而会让一个普通人不知所措,继而沉沦,然后死亡,他们来得晚、死得快,留下的都是残缺不全的尸身。
2000年11月15日,星期三,这天早晨,埃多阿尔朵·安杰利像往常一样很早就醒了,然后他身着睡袍踱至窗边,仰望着天空,就和每个普通的早晨一样。我们无从知晓他对天空如此着迷的原因,究竟是喜爱天空的变幻莫测,还是对天空那种无法预料的变化感到恐惧。昨夜他睡得很不安宁,这种可怕的睡眠状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周,也许是有一桩心事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他。但他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谁也弄不清他究竟为什么如此焦虑,也没有人会想到:死亡会突然降临。就在他的尸体被发现后,他的一位朋友告诉警察,埃多阿尔朵曾在当天上午和他通过电话,当时他显得很轻松,甚至他们还约好当天下午见面。
这是在10点30分,高速公路的守护人员在佛萨诺(Fossano)高架桥下找到了埃多阿尔朵·安杰利的遗体。当警察找到埃多阿尔朵·安杰利的汽车时,引擎尚在转动,司机座的门也大开着。意大利举足轻重的大工业家乔万尼·安杰利二世(人称吉安尼)的儿子就这样出人意料地死了。埃多阿尔朵是在这天早晨七点十五分坐上了他的菲亚特克洛玛(Croma)房车,从图林朝位于热那亚西南部利古里亚(Ligurien)区海边的萨瓦纳(Savona)方向驶去。在车里,他曾心情平静地用手机打了好几个电话,其中几位是他的旧友——这些电话看起来不过是些平常的通话,但对埃多阿尔朵而言,这显然是一种告别:简洁的、平静的、生活式的告别仪式。但是,从另一面说,他的举动却更像是命中注定,他拥有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疯子埃迪”。这是他的朋友们赠送给他的,因为在他富有的朋友圈子里,他的举止怎么也让人难以理解,他的家族是这样显赫,而他却似乎总是处在某种阴影里,他显得如此矛盾:既自卑又狂妄自大,有时龌龊得像个乡巴佬,有时又恢复了贵族的高雅。于是他更像一个堂吉诃德似的矛盾复合体,没有人同他较劲,但他却总是在同自己的另一面对垒。埃多阿尔朵也曾在1985年最后一次努力尝试继承父业,但和以往一样,最后也不了了之,最终他还是不愿过那种家族为他所选择的生活。
也许,如果埃多阿尔朵将要继承的是一个铁匠铺的话,事情会更好。但据经济杂志《福布斯》FORBES 2000年6月刊的估计,这份遗产价值高达50亿欧元。而埃多阿尔朵生前的言论或许是他对庞大产业毫无兴趣的最佳诠释——他藐视资本主义,对此他在面对各种记者采访时都丝毫不加以掩饰,他认为金钱对于资本家来说就好像是生活必需品一样,他们被迫不断地谋求利润。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本性,一种不断谋求最大限度利润的本性,而正是这个本性又导致了我们这个世界蒙受金钱、嫉妒、贪污腐化的污染。
自出生那天起,这位家族王子就毫无生活压力,他拥有庞大的家族产业,完全没有普通人在金钱上的苦恼。然而埃多阿尔朵却同时拥有一颗喜欢自我探寻的、哲学的心,这使他敏感、多思,与众不同。也许正是由于见惯了家族成员拥有不尽的财富,却仍然对金钱不知疲倦地追逐,这种贪得无厌的表现使得这位王子对资本主义的厌恶逐渐加深。平时,他根本无心过问经济和金钱事务,而是沉湎于研究宇宙和人类的本源这样的抽象问题。为了找寻自我、找寻世界的内在联系,他曾周游了印度和非洲大陆。1990年,这个腰缠万贯的年轻富翁在肯尼亚因携带300克海洛因而被捕,家族只好通过外交途径将他从肯尼亚的监狱里解救出来。也正是这一时期,因为性格的怪僻,他的父亲终于完全放弃了让他成为家族帝国继承人的念头。
多年来,埃多阿尔朵在背离金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每当他被问及家族和家族的经济帝国时,埃多阿尔朵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他的金钱观让人联想到著名的化募修道士的传道,这绝非偶然,因为埃多阿尔朵·安杰利不但是虔诚的教徒,而且是方济各会的追随者。这很有可能处于某种同病相怜的原因——方济各会创始人佛朗士·冯·阿西西(Franz von Assisi)就是因不愿承接家业而断绝了与父亲的关系,后来他的朋友们追随他,共同组成了“小兄弟会”。这些化募修士开始了漫游四方、传达上帝的信旨的生活。1223年罗马教皇赫诺留斯三世(Honoriius III)宣布承认这一宗教派别,1226年佛朗士·冯·阿西西去世。
警察在他的汽车里没有发现任何交通事故的痕迹,高速公路的护栏也是完好无损,看来,埃多阿尔朵·安杰利是非常从容地停下车,翻过高架桥的护栏,然后纵身从高达80米的高速公路上跃下。警察在他的衣袋里也没有找到任何遗书,只找到他的驾驶执照。那天早晨,埃多阿尔朵·安杰利内着睡衣裤,外套一件灰色灯芯绒外套,这都是平常的装束,没有丝毫隆重、体面、预示某种重大心理决定的服饰。
第二天,意大利的所有报章充斥着有关安杰利继承人猝死的消息,意大利最显赫的家族,其“王储”之死不仅是花边新闻,也是市民真正所关注的事件——因为安杰利家族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引起意大利的变化。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如此悲剧?消沉的儿子选择自杀的途经来结束生命,他显赫的父亲又该对此承担怎样的职责呢?为什么恰恰安杰利家族的成员会如此命运多舛?“王储”的死对意大利家族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呢?谁能率领“王室”进入第三代呢?意大利唯一的汽车制造商也会变成像可口可乐、雀巢、IBM计算机、通用汽车这类庞大、但却无名无姓的跨国公司吗?
和许多大家族一样,始料未及的死亡总是与安杰利家族如影随形,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的死像埃多阿尔朵·安杰利之死给家族以如此沉重的打击,因为家族中尚无一人是以自杀的形式告别生命,而且,他本应该是这个家族的“王储”。
一周以后,葬礼在家族祖居的菲拉·佩洛莎(Villar Perosa)举行。这是一个充满悲哀而又简洁的葬礼,持续了仅仅一个钟头,只有埃多阿尔朵和家族的密友出席。安杰利家族的保镖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分布在家族居所的周围,几位摄影师也被隔离在安全距离以外,他们只好使用长焦镜头。第二天报刊上登出的照片是满头华发的父亲吉安尼,他的右手持着拐杖,左手由妻子玛芮拉·卡拉奇奥罗·迪·卡斯塔列托搀扶,儿子辞别尘世时母亲正在家族的第二故乡纽约;另一张照片上是吉安尼的弟弟乌姆贝托和妹妹苏珊娜,两人低垂着头步入菲拉·佩洛莎新古典式的教堂,他们的背脊似乎让沉重的悲哀给压弯了,脸上仍满是震惊的神色;还有一张埃多阿尔朵的侄子约翰·艾尔坎的照片——显然,在众多的家族成员中艾尔坎的照片被置于显著位置绝非偶然,记者们早已猜测他有可能取代埃多阿尔朵的“王储”位置。后来被证实,记者们的猜测没错,他果然被指定为吉安尼·安杰利的继承人,成为家族的首脑。艾尔坎的母亲玛格丽塔是埃多阿尔朵的妹妹,她也从生活多年的巴黎赶来参加葬礼。
在这场简单灰暗的葬礼上,老迈的吉安尼·安杰利在哭泣,他的泪水不停地流下面颊,此举在公众场合是前所未有的,据葬礼第二天的报:刊报道,吉安尼·安杰利在低声啜泣:“我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
11点30分安魂弥撒结束后,埃多阿尔朵的棺木被抬出了教堂,天下着雨,教堂门前是一片花圈的海洋。这片海洋中有意大利总统卡罗·阿塞格利奥·齐阿姆皮(Carlo Azeglio Ciampi)赠送的,也有菲拉·佩洛莎当地居民赠送的,还有一个系着蓝色缎带的花圈是菲亚特公司全体员工赠送的,几公里开外的菲亚特工厂工人此时也停工默哀。
埃多阿尔朵被安葬在家族墓地中。安息在此地的已有菲亚特帝国的奠基人乔万尼一世、他的妻子克拉拉和他们的儿子埃多阿尔朵(即吉安尼的父亲)、还有乔吉奥(吉安尼的弟弟)。
葬礼过后,全家人回到住宅中,屋外的一切似乎又回复了原样,一位园丁开着小型拖拉机穿过柔软的草坪,收拾着秋天的落叶。
几辆警车守护着通向菲拉·佩洛莎的街道,警察们都默默无语,各自陷入了沉思——这种沉思显然不是出于职责要求或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而是因为整个菲拉·佩洛莎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与安杰利家族息息相关。他们此时无须驱逐好奇的来客,因为这天根本没有来访者。家族的住所位于皮内洛罗(Pin-erolo)和塞斯特利勒(Sestriere)之间,距离图林50公里,位于海平面以上530米处,空气中弥漫着百里香和迷迭香的气味,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飞鸟。这是一个家族的圣地,也是家族安详之地,在菲拉·佩洛莎市政府门前端坐着一尊青铜雕像,纪念着意大利最大的汽车制造商菲亚特帝国的奠基人。
以往,在距铜雕不远处的长凳上每天傍晚都坐着的四位老先生,他们每天谈论的话题也是周而复始:塞利亚(Seria)甲级队的上场比赛、意大利国内的贪污腐化、大自然的美丽、以及后来成为意大利总理的希尔维奥·贝鲁斯科尼(Silvi Berlusconi)的勃勃野心。但在这个11月的傍晚,他们相互却很少交淡,一种莫名的悲伤笼罩了整个小镇,而如果他们开口的话,安杰利“王室”的悲剧则成为唯一的话题。对于他们和菲拉·佩洛莎所有居民来说,安杰利家族显然就是意大利的另一个王室。
“悲痛不会因为显赫、富贵而有分毫减少!”其中一位这样说道,另外三位点头称是,然后他们又都各自陷入沉思中。
坐在这儿的四位老先生是皮蒙(Piemont)山区的田园般的小镇菲拉·佩洛莎的居民,这是一个人口只有四千的小镇,在进入小镇的路口高悬着一块牌子,欢迎来客一上面写着:人造时世,时世造人。这里就是安杰利家族的世居之地,这个对意大利的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对意大利的经济产生极大影响的家族一直保留了在当地的祖居。当笔者想从这几位老人那里了解有关安杰利家族的时候,那几位老先生显然不愿对一个外乡人多谈有关安杰利家族的事,他们不想因此而背上搬弄口舌的嫌疑。“如果您想写安杰利家的事,”其中一位解释道,“您必须征得他们家的同意。”另外三位老人对笔者的询问充耳不闻,他们转过身迎向正好经过的家人,像每个礼拜天一样,他们去圣皮埃特罗教堂(San Pietro)望弥撒,圣皮埃特罗教堂是当地的两处教堂之一,两处教堂均由安杰利家族出资维修过。
布瑞洛咖啡馆
吉安尼·安杰利并没有在菲拉·佩洛莎停留多久,到了周末,这位家族首脑就乘直升机离开了潮湿阴冷的图林,前往空气清新的西则那河谷(chisonetal)。这儿的人告诉我:有时候,吉安尼·安杰利礼拜天也会来这个小镇做弥撒,弥撒过后还会和其他教徒聊上几句,此时的他和镇上的其他居民几乎没有分别。
今天,这个小镇对吉安尼来说就像当初对他的祖父吉乔万尼·安杰利一世一样,是心灵的避难所。菲拉·佩洛莎是家族的灵魂所在地,此地远离全球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安杰利家人在这儿能够静心沉思;菲拉·佩洛莎也是家族聚餐的地点,许多重要的决定都是在这儿做出的;此外,不管是哀悼还是庆典,在菲拉·佩洛莎家族的住所里,安杰利家族成员总是济济一堂。
说起这个家族的祖居地,那还要从家族的奠基人开始说起。
菲拉·佩洛莎本来属于皮科那·德拉·佩洛莎伯爵(Graf Piccone della Perosa),吉安尼的曾祖父埃多阿尔朵一世(死于1871年)于1853年从佩洛莎伯爵的继承人手中买下了这块地产,此后这片土地就成为安杰利家族的世居之地。尽管这个小镇仍然沿用了佩洛莎伯爵的姓,但安杰利家族实际上早已深深地影响了菲拉·佩洛莎。在整整一个多世纪的生活中,安杰利家族的影子在这个小镇上随处可见,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佩洛莎的几乎每个居民、至少每个家庭都有一位家庭成员曾经为安杰利家族的企业工作过,这个小镇其实更应该被称之为安杰利,而不是什么佩洛莎。
在乔万尼一世之前,安杰利这个姓根本不起眼——在今天,在意大利乃至整个世界,安杰利这个名字就是金钱、权力、上流社会的象征,而它优美的意大利语发音又使它充满诗意。但实际上“安杰利”这个词在意大利文中是名词agnello的复数形式,而且这个古老的名词原本丝毫不能让人敬畏,因为它的本意为:羔羊,一个似乎根本与金钱和权力毫无瓜葛、甚至意味着贫穷的词汇,与其说它代表着权力与财富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牧羊人的名字。但在今天,安杰利这个曾经卑贱的姓却成了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这也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家族的发家史:在过去的100年中,安杰利家族成员以其智慧、胆识和善于与权力攀亲的手段而不断拾阶而上,最终进入了意大利的权力中心。当然,这绝非一帆风顺,安杰利家族为此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痛苦也同样令人惊愕。其实这个家族和世界许多大家族一样,甚至和那些辛勤劳作的普通员工一样,他们也曾为了生存、发展而一步步努力,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劳动。
安杰利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公元700年,这个家族源于何处,现已无从考证。据推测,该家族发源地可能是那不勒斯或者曼图亚(Mantua)地区,以往这个姓氏从来没有成为历史博物馆中的一颗星辰,直到1830年左右,吉安尼的曾祖父埃多阿尔朵成为家族被载入史册的第一人,他就是安杰利王朝创始人之父。
埃多阿尔朵·安杰利曾是菲拉·佩洛莎当地很有名望的农场主,他的妻子名叫阿妮切塔·弗利塞提,他在自己的农庄里养蚕,喂养牲畜。他们的独子乔万尼出生于1866年8月13日。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