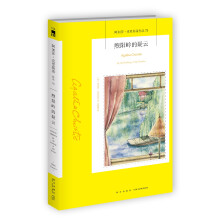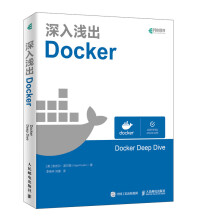1937年的第比利斯。我的妈妈安娜·雅科夫列夫娜.普里马科娃,是一位专业水平颇高、医德非常高尚的妇科医生,她社交广泛,待人诚恳、友善。凡是与我母亲相处或共过事的人们,都对她赞不绝口。她的弟弟A.雅科夫列维奇同样也是一个妇科医生,但却在巴库被捕,后来在第比利斯被杀害了。其实,他这个人根本不过问政治。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说他参加过“反苏组织”的一个重要“物证”是搜查中发现了一把旧俄军官佩剑,因为他在“十月革命”前几个月曾是旧俄贵族士官。
妈妈的兄弟姐妹很多,除了雅科夫列维奇和一个妹妹外,其他弟妹早都死了。其中,一个弟弟在日俄战争中阵亡,另一个弟弟从前线回来后死于肺病。一个妹妹的丈夫是出色的内科医生Ⅱ·A·基尔申勃拉特,曾任柏林大学高级教授。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是他早逝的前妻所生,只有老三是我的姨妈所生。老三叫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也是一名医生,还是一个热诚的布尔什维克,是第比利斯一家大医院的急诊部主任。有一次,从埃里温运来了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汉齐扬的尸体,要求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做出“死者是自杀身亡”的医鉴结论。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因拒绝这一要求而被捕,接着也被枪毙了。
当年在第比利斯的深夜里,到处可听到汽车在这家或那家门前停车时的刹车声。我们居住的列宁格勒大街并不怎么大,长150米,只有13家住户,所以各种悲剧的发生是全街人都有目共睹的。当时住在5号楼的列·陀斯托耶夫斯基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电影导演,他的影片《我住的那栋楼》、《当小树长大的时候》等被列入了苏联电影的经典。1937年时,我们一群小男孩经常悄悄躲到二层他家的窗户下张望,因为听说他母亲被捕时还向逮捕者开枪,而对我们来说,感兴趣的不是这位妈妈有多么勇敢,而是她用的是什么手枪,是不是“勃朗宁”手枪?
我是我母亲唯一的儿子。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她活着也是为了我。她生我时年事已高,如果她有什么事被捕的话,很难想象我会遇到何种厄运。
我当时对已经发生的事反应如何呢?我们同代人的某些代表人物坚信,即使当时是小孩子,长大后也会明白当年发生的事情。我不属于那种未卜先知、明察秋毫的人。当时,我母亲作为医生与来院治疗的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伊留申的妻子相识,后来她俩成了好朋友。我听说伊留申被捕了,为与他划清界线,就拿起剪刀将他在我生日时送给我的手枪皮套和背带剪成了碎块。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不管时间如何流逝,悲剧性的1937年始终折磨着母亲的心灵。她在一家铁路医院工作,是妇产科高级医生。由于许多地方需要她,她又轻松地在第比利斯纺织厂妇幼保健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连续工作了35年。工厂距市中心很远,战争期间母亲又担负了一项工作,到城市的另一端上班。劳累一天,晚上回家时已筋疲力尽。在所有人都很艰难的战争时期,母亲如此奔波,完全是为了我的温饱。
母亲不参加任何党派,小心翼翼,从不说过头的有刺激性的话,更不喜欢谈论政治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在政治上很幼稚。我还记得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已经是大学生的我回第比利斯度假期间与母亲谈起斯大林时,她的一番话令我感到吃惊和恐惧。她说“斯大林是个残暴的杀人凶手”。我惊讶地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难道从这个‘粗鲁残暴的人’的著作中看出什么了吗?”母亲那种心平气和的回答使我感到既震惊又沮丧。她说:“我才不读他的书呢,你可以去告密——他喜欢这种做法。”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谈论过类似的话题。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