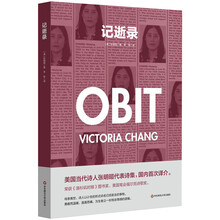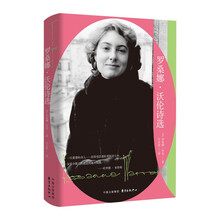一 寻找那段时光“只有当我踏进外省的那些旅馆,我才感到幸福,那些房间里有一股陈朽的芳香,风将它们吹散,却无法根本抹去;在那里,每当晚上我们打开房门,感觉就像擅自闯进了一个原本在那儿的、散乱的人生,当门又关上时,我们一边用手勇敢地抓住这人生,一边往更里面走,一直走到桌旁或窗边,然后,在随意散漫中坐下来,坐在那个长靠背沙发上,省城的绒绣工人把它做成想象中巴黎的摩登式样,现在,我们可以尽情阅览这个人的生活了,不用丝毫局促不安,全然自在地,就像主人一样,赤脚走在他无名的地毯上,在这个角角落落都充斥着别人灵魂的房间里,就连壁炉前柴架的形状和窗帘上的花饰里,都保留着他们的梦迹;这个神秘的人生,当我们浑身颤抖地去插上门闩时,感觉就像把他关在了这里;现在,又把他推到了自己面前,最终和他一起躺到了床上那白色的大被单里,被单从上面向你呈现出他的面孔,而此时,就在旁边,教堂的钟声响起了,向全城昭示着那些垂死之人和恋爱者失眠的钟点。”我们这位充满幻想、敏感的旅行者是如此浮想联翩。可如今,这家破败的旅馆已经被分割成了一些私人公寓。但就在那套房间里,整整一个夏天,我曾有幸聆听到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出自一个最和谐悦耳的声音。一九0六年的黑塞瓦尔,我不敢说有多美,但却最纯粹地体现着凡尔赛的传统。那里保留着凡尔赛被“慷慨的洛克菲勒”的那些愚笨的追随仿效者们大肆败坏后的古色余韵,而今天的凡尔赛,它那陈旧迷人的外省韵致已被日行千里的汽车破坏殆尽。感谢上帝,那时黑塞瓦尔旅馆的地位还没有被现今的特里亚农豪华饭店(多亏了玛丽一安多奈特彩带飘飘的牧羊鞭)取代,虽然我们当时在那里很不舒服。这些年里,在一波又一波、无法计数的、接连不断的浪潮冲击下,黑塞瓦尔一点点被废弃,终至卖掉。我们向来是这样,为了薄古厚今的现代人的方便快捷,而最终抛弃历史的遗迹。我是否该承认?通向那段时光的道路既艰难,又充满温情。太多的记忆已经变得稀薄而苍白,遗忘的眩晕使我再也无法看清那个堂皇的门厅——那些门都开向哪些厅堂?那独特的回声来自哪道长廊?是哪面墙上的纹饰,边沿金粉退色发霉又散发出香气?阴影掩住了哪条走廊的尽头?脚下碰触到哪张地毯的裂缝?——对这一切,我曾是那样熟悉。我只记得一个大房间,夜色从两扇落地窗袭进来——那是我亲爱的马塞尔的房间,隔壁住着他忠心的女仆费丽斯,毗邻的还有一个房间……也许不止一个,不是吗?可是?……那里总散发出不知名的烟熏的芳香。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