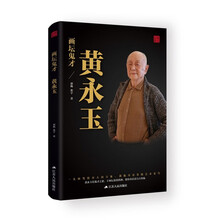我蹒跚在炎黄艺术馆黄胄铜像前,数一数日子,一转眼,他已经离开我们11个寒暑了。我想清理一下,在这段时间里,我为他做了些什么。其中有我大胆写了这本近30万字的回忆录。说实在的,我原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位美术编辑,对于小说、诗歌只有欣赏品评的份儿,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写文章、写小说,我自知没有那份天才。但是无情的病魔过早地夺走了黄胄的生命,一想到我再也没有了他为我挡风遮雨的日子,就更加感到悲痛。在此同时,有人说我有丰富的素材,劝我为他“立传”。黄胄堂兄梁斌哥说过我应该学着写点东西。但我不是作家,对于写传记的道道,我更是一窍不通。写得不好,不也是糟蹋纸吗。我没有信心,犹豫不决。但是和黄胄共同生活的47年的痛苦与欢乐的情景,却使我不能忘怀。我经常魂牵梦萦,追忆起那段日子的种种细节,有时也有冲动想把它们写出来。
1997年10月,黄胄已逝世半年了,也许是我过度悲伤,流泪太多,也许是他交给我继续完成他未完善的炎黄艺术馆面临的种种困难使我压力太大。也是23日的夜晚,我的左眼巨痛。第二天早晨睁开眼,左眼一片火红,伴随着疼痛,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医生说是青光眼急性发作,极有可能左眼失明。在治疗的过程中,我沉下心,决心把我们共同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写出来。经过一年的时间,我写出了约30万字的一大摞稿纸。对于能否出版,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请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曾经为《红旗谱》、《红岩》、《李自成》等名著书籍作过编辑的张羽先生看一看,因为他也是黄胄的朋友。但他那时已年近80,加上文革对他的冲击,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因此他回绝了。在我再三请求之下,他答应看一看,但不作任何加工修改。过了几天,他通知我去拿稿子。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他家,没想到他对我写的书稿大加赞扬。在一些章节里,他还批注了“好”或者“细碎”等字样。他还建议我把第三章“经历磨难”改为“红与黑”,但是我当时没有那个“胆”,所以保留了原样。经过他的指点,我有勇气了,也写快了。出版之后,经过一些熟悉黄胄的人和我在出版社原来一些资深的文字编辑阅读,我得到不少表扬,但是也提出不少宝贵意见。我在这次再版之前又做了不少认真的修改和补充,比以前似乎更明朗了一些。
总结这本书,我觉得正因为本人不是作家,也不想当作家,只是把读者当作我和黄胄两人的朋友,我只是在和朋友们倾诉,倾诉我们的爱情,我们遇到的坎坷、不平。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有形无形的挑战,其中有所创造的成绩和不能磨灭的伤痕。我是情真意切,没有矫揉造作和煽情。但是也正因为本人不是搞文学的,对于文学的基础太差,不能充分表达我要说的和想说的。其实黄胄这个人可爱的亮点和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还有很多。由于我的水平,我没能写出来,真是挂一漏万了。还有一层原因,虽然我从青年到现在,没有离开过美术这个大行当,和黄胄及我们同代人参加过意识形态领域里大小不同的政治运动,有、的是很严酷的。在运动的风潮中涌现出的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人物和事件,有的以“马列主义”的捍卫者自居,专门吓唬别人;有的言不由衷,伤害别人;有的本是才华横溢,但经不起折腾,在生活中变得一蹶不振,甚至英年早逝;有的真的是马列主义者,讲究实事求是“惜才、爱才”尽力保护一些文化人,有时因时局所限,他们也只能扼腕叹息。这些个人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社会群体。黄胄和我共同生活在这个群体中,我们的言行受到这个群体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来或悲伤或乐观的情绪也是极为复杂的。但是因为我的思想和艺术永平限制,我虽然在书里梳理描述了一些,但是有些事,我当时就是困惑的,现在仍在困惑中。我不能给朋友们说清楚,把黄胄所有的事件的方方面面描写清楚,尽管我尽了些努力,这是我感到遗憾的。
反正我已经写出来了,并翻译成了英语版,这也许是我对我的丈夫——黄胄最好的爱情献礼。希望朋友们读完拙作有所收益,也希望给我批评,厉害一点也不要紧。 郑闻慧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