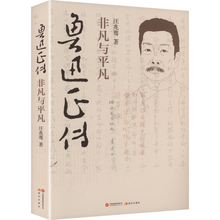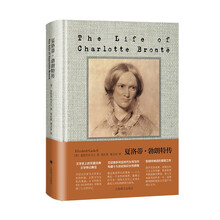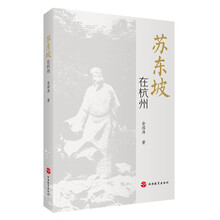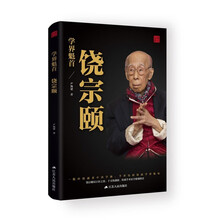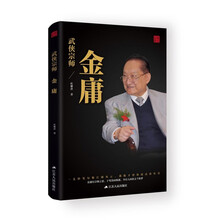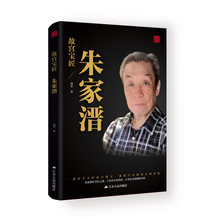曹家从曹雪芹六代祖、五代祖从龙入关之后一直定居在北京,至曹雪芹时已是百年有余。说曹雪芹是北京人、北京作家,与近百年"祖籍"争论没有任何矛盾。
曹雪芹在北京这块热土上,倾其一生心血,奉献了一部罕世之作--《红楼梦》。《曹雪芹在北京的日子》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曹雪芹、认识曹雪芹、记忆曹雪芹的窗口,是献给所有关心中华文化的世界各国朋友们的一份特殊礼物!
《曹雪芹在北京的日子》编选吴恩裕、端木蕻良、曾保泉、胡文彬等人有关曹雪芹在北京生活、著述的主要经历的重要文章,搜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进行了严谨有序的论证分析,结合众多的相关民间传说,全面展现了曹雪芹在北京数年岁月的全貌,有散记、考析、故事,共十九篇,析为三卷。
卷一"燕市寻踪",收入专文六篇,作者们以相关清宫档案史料为根据,实地访寻曹雪芹在北京的游踪、住处,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寻梦"线路图。
卷二"著书西郊",选文五篇,作者们以敦敏、敦诚、张宜泉的诗文为线索,结合实地踏勘和民间传说,对曹雪芹"著书西郊"的迁徙路线与著书环境作了全面的考察。
卷三"曹雪芹的故事",是著名学者、红学家吴恩裕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的"曹雪芹小传",构思巧妙,文笔优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高度评价。
《曹雪芹在北京的日子》卷一和卷三共附录六篇,目的是向读者提供可资参考的史料。其中后三篇尚有争议,敬请读者自辨。
展开